[吉多加]“大诗”与史诗:藏族叙事传统的文类比较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4-08-28 作者:吉多加
摘要:“大诗”与史诗是东西方文类系统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与藏族叙事传统相关的两个文类关键词。作为源自域外的概念术语,国内学者在阐释和解读过程中出现了对两者进行混淆或等同的现象。两者表面相似,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从文本分析和文类比较层面阐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我们进行文类划分和范畴界定的必要路径。
关键词:“大诗”;史诗;藏族叙事传统;文类比较
在藏语中,“大诗”(mahākāvyā)被译作 或
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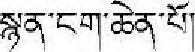 ,现今后者通用,而史诗(epic)一词,则有若干种翻译,(1)至今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从叙事的宏大、主题的崇高、结构的完整诸方面,两者无疑具有相似性特征。著名学者范德康、朝戈金也在论文中阐述过相似的观点。(2)在藏族叙事文类的概念引入上,“大诗”先于史诗,因此当代藏族学者把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称作“大诗”。(3)然而,这个术语的转借却把“大诗”的涵义宽泛化了,因为在被称之为“大诗”的古典梵文叙事诗中并不包括上述两大史诗。有的学者把《格萨尔》也称作“大诗”。(4)正如格萨尔史诗在汉语接受语境中经历“野史或传说故事说”、“诗史说”、“小说、长篇故事说”(5)一样,藏族传统“大诗”作品也常被冠以“长篇小说”的头衔。
,现今后者通用,而史诗(epic)一词,则有若干种翻译,(1)至今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从叙事的宏大、主题的崇高、结构的完整诸方面,两者无疑具有相似性特征。著名学者范德康、朝戈金也在论文中阐述过相似的观点。(2)在藏族叙事文类的概念引入上,“大诗”先于史诗,因此当代藏族学者把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称作“大诗”。(3)然而,这个术语的转借却把“大诗”的涵义宽泛化了,因为在被称之为“大诗”的古典梵文叙事诗中并不包括上述两大史诗。有的学者把《格萨尔》也称作“大诗”。(4)正如格萨尔史诗在汉语接受语境中经历“野史或传说故事说”、“诗史说”、“小说、长篇故事说”(5)一样,藏族传统“大诗”作品也常被冠以“长篇小说”的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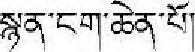 ,现今后者通用,而史诗(epic)一词,则有若干种翻译,(1)至今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从叙事的宏大、主题的崇高、结构的完整诸方面,两者无疑具有相似性特征。著名学者范德康、朝戈金也在论文中阐述过相似的观点。(2)在藏族叙事文类的概念引入上,“大诗”先于史诗,因此当代藏族学者把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称作“大诗”。(3)然而,这个术语的转借却把“大诗”的涵义宽泛化了,因为在被称之为“大诗”的古典梵文叙事诗中并不包括上述两大史诗。有的学者把《格萨尔》也称作“大诗”。(4)正如格萨尔史诗在汉语接受语境中经历“野史或传说故事说”、“诗史说”、“小说、长篇故事说”(5)一样,藏族传统“大诗”作品也常被冠以“长篇小说”的头衔。
,现今后者通用,而史诗(epic)一词,则有若干种翻译,(1)至今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从叙事的宏大、主题的崇高、结构的完整诸方面,两者无疑具有相似性特征。著名学者范德康、朝戈金也在论文中阐述过相似的观点。(2)在藏族叙事文类的概念引入上,“大诗”先于史诗,因此当代藏族学者把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称作“大诗”。(3)然而,这个术语的转借却把“大诗”的涵义宽泛化了,因为在被称之为“大诗”的古典梵文叙事诗中并不包括上述两大史诗。有的学者把《格萨尔》也称作“大诗”。(4)正如格萨尔史诗在汉语接受语境中经历“野史或传说故事说”、“诗史说”、“小说、长篇故事说”(5)一样,藏族传统“大诗”作品也常被冠以“长篇小说”的头衔。 此外,国内其他学者也在讨论中出现含糊不清或混淆两者的现象。如《印度大诗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尽管把两大史诗以及《往世书》等称作“大诗”的源头,但在实际研究中却把它们都纳入到“大诗”文类下,并且认为“印度大诗,叙事宏大,如海如河,是印度古代集体创作的自觉选择”。(6)口耳相传的印度叙事传统和人民大众的集体创作,固然是“大诗”宏大叙事的土壤,但从叙事规模、叙事法则、叙事要素、作者身份等诸多层面,“大诗”和史诗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不能混淆或完全等同。
一、“大诗”和史诗:文本比较和分析
文本分析是文类概念阐释和范畴界定的基础性任务,因此,为了具体而直观地体现“大诗”和史诗文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首先要对两种文类的代表性文本,即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与古印度和藏族学者基于两大史诗创作的“大诗”,以及藏族史诗《格萨尔》和其他原创“大诗”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为其理论话语和学理阐释奠定实践基础。
(一)史诗《罗摩衍那》与“大诗”《罗摩衍那传》
印度传统上把《罗摩衍那》称作“最初的诗”(ādikāvya),蚁蛭称作“最初的诗人”(ādikavi),(7)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书面文学。《罗摩衍那》精校本校刊者之一,印度学者威迪耶(P.L.Vaidya)把印度两大史诗等称作“伶工文学”(Bardic literature),其特点就是这些作品都包含着许多短歌、短的叙事诗和叫做赞颂诗(GāthāΝārās'aṃsi)的赞歌,都由到处游行的伶工歌唱,代代口耳相传。(8)玄奘于7世纪前半叶在印度所见到的《罗摩衍那》只有现在版本的一半长,这就可以说明它经过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分散到统一、格局短小到体量庞大的发展演变过程。很多学者认为《罗摩衍那》第一篇和第七篇形成时间晚于第二篇至第六篇。(9)第一篇和第七篇里讲到罗摩的两个儿子和蚁蛭的两个徒弟俱舍和罗婆兄弟俩专门以唱《罗摩衍那》为生,他们俩又传给自己的徒弟,师徒授受,口耳相传。“流传既久,既广,歌唱者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听众,根据不同的听众的反应,为了取悦于听众,临时即景生情,增加上一些新的诗歌,比如自然景色的描绘,战斗场面的描绘,这都极容易挑动听者的心弦,拉长的可能就更大。输洛迦又是一种比较容易操纵掌握的诗体,临时增添上几首,是并不困难的。”(10)《罗摩衍那》被称作“最初的诗”,主要是着眼于艺术形式上的变化。与《摩诃婆罗多》一样,它也主要采用通俗简易的输洛迦体,但其语言在总体上比后者精致一些,辞藻繁缛,风格华丽,开始出现讲究藻饰和精心雕镂的倾向,相比后者更接近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史诗概念。这种语言艺术特点在后来出现的“大诗”中得到充分体现,(11)这说明“大诗”的艺术特征直接导源于《罗摩衍那》,它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4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有两万四千颂,现代精校本有两万颂。据统计,其共有两千多种手写本,有五十多种梵文注释,(12)这是口头进行演述的典型特征,是书面文学所无法企及的。
印度梵语“大诗”中取材于《罗摩衍那》的有《罗怙世系》和《跋底的诗》,前者充满绚丽多彩的画面和情味,具有优美的语言和韵律,被奉为古典梵语“大诗”的典范;(13)后者不仅是一部“大诗”,叙述罗摩衍那的完整故事,同样也是一部语法修辞著作,提供各种语法规则和修辞方式的例句。在藏语文学中,象雄·曲旺札巴(1404—1471)所著《罗摩衍那传》(1438)是根据史诗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虽然没有分章节,篇幅也不算特别宏大,但基于其诗学特质和修辞风格,我们不妨称其为一部“大诗”。全诗共有1020行诗句,除去前言后跋51行,正文有969行,其故事情节与敦煌文献中的《罗摩衍那》藏译文基本相同,因此很有可能是根据这个译文创作的。(14)相比史诗庞大的叙事体量和复杂的故事情节,这部“大诗”仅仅截取其中的主干情节,围绕罗摩、悉多、魔王罗那波三位人物叙述,对故事情节没有过多的铺展,诗人更注重于诗律的锻造和修辞的运用,全诗充满《诗镜》中的双关、颠倒、夸张、排比、复叠等种类繁多的明喻和隐喻修饰法,充满层出不穷、花样繁复的文字技巧,使用辞藻学中的同义异名,使得全诗辞藻华丽、形式雕琢、风格优美,并且由于过度追求修辞和诗律,不少诗句显得晦涩难懂,对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想要完全理解它的诗句和用意,不仅要熟悉史诗的故事情节,更要对《诗镜》为准则的藏语诗学理论和修辞手法有娴熟的学习和锻炼。
(二)史诗《摩诃婆罗多》与“大诗”《般度五子传》
史诗《摩诃婆罗多》成书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有精校本、通行本等多种版本。在八百年的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史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后来演变成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最后扩充为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现在的精校本有八万多颂,(15)其内容主要叙述婆罗多族的后裔般度族和俱卢族围绕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的内涵和体量完全溢出了西方英雄史诗的概念范畴。印度传统上称其为“历史传说”(itihasa),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而是神话化的历史,(16)是诗(kāvya)、论(s'āstra)、传承(smrti)的三位一体。它是以诗的形式吟唱印度古代历史传说,涉及创世神话、帝王谱系、政治制度、宗教哲学、律法伦理和天文地理,这些内容都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也就是说,它以古代英雄传说为核心全方位地记述印度古代历史,是印度古人在没有书写习惯的条件下记述历史和文化叙事的一种特殊手段。(17)
故事取材自《摩诃婆罗多》的古典梵语“大诗”《野人和阿周那》和《童护伏诛记》,前者描写般度族五兄弟流亡森林期间的故事,其中不仅充满争执、战斗、风景、苦行,也涉及仙女的诱惑和色情的描写;后者叙述童护在大殿众王面前不服黑天,侮辱了他,因而被黑天杀掉的故事,其中有外交、决裂、宣战等战争情节,军队前行一路景色的描写和对女人的调情,也包括迥文诗和图案诗等层出不穷、花样繁复的文字技巧。藏族学者拉敏·益西楚臣(1913—1977)所著《般度五子传》是一部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的“大诗”,(18)全诗共有557行诗句,内容主要叙述婆罗多族后裔般度族和俱卢族争夺王位的故事。与规模宏大、内容庞杂的史诗相比,“大诗”中只有两族争夺王位的主干情节,通过有限的篇幅,诗人将两族争权的故事做了一个潦草的叙述,对其内容没有展开描写,诗人注重的依然是繁复的修辞手法和奇巧绚丽的诗律锻造。
(三)史诗《格萨尔》与藏族其他原创“大诗”作品
众所周知,《格萨尔》是一个“文本内容浩瀚、话语结构复杂、文类形态多样、传承方式众多,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圈流传的宏大叙事传统”,(19)就其体量而言,已经有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170多部文本,被誉为世界上篇幅最长、规模最大,依然以“活态”传承的史诗之一,与《江格尔》《玛纳斯》并称为我国“三大史诗”。作为藏族口头传统的继承者,史诗构建了11世纪的传奇英雄人物格萨尔,以氏族部落社会的征战和英雄业绩为核心叙事,摹仿、挪用、借鉴来自古老叙事传统“仲”(髸D)的各种主题、模型、要素、结构、程式,把起源神话、氏族形成、民族历史以及宗教叙事融入其中,从而把作为历史话语的史诗“本事”塑造成具有庞杂时空、宏大结构和神圣主题的叙事文本,成为地方知识、族群记忆、民间智慧、母语表达、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仲”起源于本土,发展于民间,与原始宗教信仰紧密相连,事关赞普神话和王权叙事,是神圣和世俗结合的文类形态,最终孕育出《格萨尔》这样浩瀚的史诗。诺布旺丹将《格萨尔》史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概括为“从历史、隐喻到象征”,提炼为“历史神话化和神话艺术化”,“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观念”的演变过程。(20)史诗虽然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文本化和固定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书面文类“南木特”(魓XPb)和“朵觉”(?BfV箦Q)的头衔,其文本中夹杂和融入更多的书写文化特点和要素,但它依然作为口头叙事在传承,由掘藏、圆光、神授、智态化、顿悟、闻知等多种史诗艺人演述,书面化史诗文本中依然能看到“仲”这一伟大口头叙事传统的延续。
藏族原创“大诗”作品则完全属于另一个传统,即书面文学,尤其是其中的《诗镜》传统。藏族学者从理论阐释和文本创作两个层面对“大诗”进行了本土化。(21)除了取自于印度两大史诗的藏语“大诗”外,另有一类以藏族历史人物为叙事对象,如仁邦·阿旺久扎的《萨迦班智达传》(1519)和拉敏·益西楚臣所著《米拉热巴传》。还有一类以完全虚构的异域为叙事空间,如朵喀尔夏仲·次仁旺杰(1697—1763)的《勋努达美传》等。“如果把《罗摩衍那传》和《般度五子传》从题材和文体风格方面看作印度‘大诗’的仿照或继承的话,那么《勋努达美传》从文体风格上、《萨迦班智达传》和《米拉热巴传》从题材和诗歌语言上都可以看作‘大诗’本土化的创造性作品。”(22)《勋努达美传》的作者在大译师达摩希日跟前学习《诗镜》理论后,根据“大诗”创作规则和叙事要素,运用韵散混合的手法创作了这部作品。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以韵散结合的形式,结合大诗创作的四大人生目的果实和创作规则,表达出世和一切皆空的幻灭思想,特别突出正法解脱思想。”(23)一方面遵从“大诗”的创作法则,描写和歌颂了城市、海洋等叙事空间,叙述了戏水、饮酒、欢爱、战争以及主角最终的胜利等情节,另一方面遵从藏族传统的叙事风格,即散韵结合的方式进行叙述,突破了单一文体方面的限制。《萨迦班智达传》和《米拉热巴传》把“大诗”题材和主人公都从印度转向藏族地区,前者分12章,多达几千行诗句,后者分12章,包括后记有677个输洛嘎,共计2708行。这两部“大诗”不仅在题材上进行了从虚构到非虚构的本土化转向,而且在创作风格方面,虽然也有种类繁多的明喻和隐喻修饰法,但比起先前的“大诗”更趋向于简单通俗的诗句,也没有完全照搬或局限于《诗镜》对“大诗”叙事要素的创作限定,摒弃重描写而轻叙述的“大诗”传统,比较自由地叙述和记载主人公真实的历史经验,使得普通读者能够去阅读和接受。(24)
二、“大诗”和史诗:文类相似性
从上述文本比较和分析能够看出,“大诗”和史诗无疑具有文类相似性,这也是较多学者混淆或等同两者的主要原因。这种相似性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去分析。
首先,最基本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大诗”和史诗都是用“诗体”,即使用韵文和格律来进行叙事的文类。婆摩诃(Bhāmaha)在《诗庄严论》(Κāvyālan˙kāra)中把“诗”分类为“分章的(大诗)、表演的(戏剧)、传记、故事和单节诗(短诗)五类”,(25)认为“大诗”就是由单节诗组成的长篇叙事诗,并对“大诗”的情节、目的,以及主人公的描写等方面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檀丁(Daṇd˙in)在《诗镜》(Κāvyād-ars'a)中把韵文体分为单节诗、组诗、库藏诗和结集诗,而“大诗”就是这些部分组成的、分章的诗,并增加了对起始、题材、场景、情节,以及人物描写方面的讨论。(26)梵语诗体的写作使用输洛嘎体,四行诗为一个输洛嘎,一个输洛嘎采用统一的格律,章节结束时,可以根据韵律和听者的需要变换音节。印度古代吠陀使用的是古梵语(吠陀语),史诗和往世书使用的是史诗梵语,而“大诗”使用的则是注重藻饰的古典梵语。(27)
史诗,在古希腊的诗学传统中,“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即扬抑抑格),取其前后长短的下冲之势,”(28)每行约有十二个轻重音,虽然不使用尾韵,但具有很强的节奏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就以格律文的形式摹仿严肃的人物而言,史诗‘跟随’悲剧;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用一种格律。”(29)因为古希腊两大英雄史诗均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这种格也被称作“英雄格”。“就格律而言,经验表明,英雄格律适用于史诗”。(30)虽然也可以用其他格律,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英雄格最庄重、最有分量。史诗的体量,也是按诗行来计算的,如《伊利亚特》全诗共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奥德赛》全诗共一万两千一百一十行。就算《格萨尔》这种韵散结合的史诗文本,也经常以诗行数来计算其体量。(31)
其次,“大诗”和史诗的相似性体现在两者叙事结构的宏大性和叙事主题的崇高性上。婆摩诃和檀丁一开始就提出,“大诗是分章的作品,与‘大’相关而成为‘大’”;(32)“分章诗也称大诗。”(33)这里所说的“大”,不仅指的是体量的庞大,诗行和章节的数量,更是指“它不使用粗俗的语言,有意义,有修辞,与善相关”,(34)“展现人生四大目的果实,主角聪明而高尚”(35)的崇高性主题。因为“大”而称其为“大诗”,所以“大”就是其最重要的文类特征和最根本的文体属性,那么,多“大”才算“大诗”呢?尽管婆摩诃和檀丁没有给出具体的章节数,但我们从《佛所行赞》(分28章)、《罗怙世系》(分19章)、《鸠摩罗出世》(分17章)、《野人和阿周那》(分18章)等文本体量就能大致看出梵语“大诗”的章节数。藏族学者对分多少章节才算“大诗”有不同的阐释,但基本上认为只要是分两个及以上章节者,都可称作“大诗”。(36)
当今史诗学者同样也在面对史诗的长度问题。(37)实际上,关于史诗长度的讨论从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了,他认为应以可被从头至尾一览无遗为限,约等于一次看完的几部悲剧的长度的总和为宜。(38)当代学者中,芬兰学者劳里·航柯(Lauri Honko)给史诗的定义是:“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起初由专业化的歌手作为超级故事来演述。它在长度、表现力和内容意义上优于其他叙事,并在功能上成为传统社区或受众群体认同表达的来源。”(39)理查德·马丁认为史诗是一个具有普泛性(pervasiveness)的超级文类(super-genre),(40)弗里称史诗为重大文类(master-genre),(41)吉达·杰克逊对作为超级文类的史诗划分出许多种亚文类(sub-genre)。(42)史诗具体的诗行数量方面,爱德华·海默斯(Edward.R.Haymes)认为普遍超过200至300诗行的长篇叙事诗均可称作史诗,而劳里·航柯则认为这样的体量不足以称之为史诗,至少应该把1000行视作衡量标准。(43)
“大诗”和史诗在面对体量来定义自身的时候,发现仅凭章节和诗行数量来定义是不够的,不能完整体现其文类本质。从婆摩诃和檀丁的论述,以及藏族学者的阐释中能看到,“大诗”除了要分章节,叙述不能过于简略,主题要崇高,还要遵循一些传统既定的叙事要素:正法、利益、爱欲、解脱为主题,英雄为主体,城市、海洋、山岭、园林为空间,戏水、饮酒、欢爱、相思、婚事、生子、谋略、遣使、战争,以及主角最终的胜利为情节。其中“风景、艳情和战斗是‘大诗’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大诗’诗人借以发挥诗艺的重要地盘”。(44)同样,因为史诗的多样性,史诗不仅体量要大,而且要从叙事场景是否宏大,风格是否崇高,题材是否重大,主人公是否有超凡的神力,内容是否与一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相联系等多方面去探讨和定义。作为一个超级文类,史诗是以谱系的形态出现的,从最典型的一端到最不典型的一端,中间有大量的居间形态。(45)也就是说,只有内容和形式,体量和风格相互结合才能定义“大诗”和史诗。
第三,“大诗”和史诗同样注重叙事结构的完整划一和文本接受者的重要性。婆摩诃指出,“大诗”要“描写谋略、遣使、进军、战斗和主角的成功,含有五个关节,无须详加注释,结局圆满,”(46)并认为如果英雄不在全诗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获得成功,那么开头对他的称颂就失去意义。这里所说五个关节,就是开端、上升、高潮、下降、结尾,是非常典型的情节设置,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47)如出一辙,而且两者均借用于各自文化的戏剧理论,前者从印度梵语戏剧,后者从古希腊悲剧。两者对情节统一性的追求,既是为了控制文本的体量来达到整齐的艺术效果,也是为了考虑听者的接受程度。檀丁认为“大诗”不能太简略,也不能太冗长,充满味(48)和修辞,诗律和连声悦耳动听,每章结尾变换诗律,而这种精心修饰的诗令人喜爱,可以流传千古。(49)同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史诗“有了容量就能表现气势,就有可能调节听众的情趣,接纳内容不同的穿插。雷同的事情很快就会使人腻烦”,(50)认为这样它就能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这种对于接受者,即听者的注重,体现了“大诗”和史诗同样作为东西方古老文体的口头性和演述性特征,即便“大诗”是完全书面化的文类,它身上也带有《罗摩衍那》等印度口传叙事的遗传属性。
三、“大诗”和史诗:文类差异性
从上述几点来看,“大诗”和史诗虽然存在文类层面的某些相似性,但基于文类属性的本质特征和文类界定的根本依据,能够发现两者具有的本质差异。
首先,叙事文本的形式方面,“大诗”是书面文本,完全由作者进行书面创作,一旦创作完成就基本固定,不会根据读者和环境的不同而改变,一部“大诗”只有一个文本,固定性是其特征。《诗庄严论》和《诗镜》着重探讨的就是文学语言的修辞手法,将装饰语言音义的修辞手法视为文学语言不同于口头语言的重要标志,比起口头文学中古老质朴的修辞手法,作为书面文学的“大诗”修辞更趋精致、更加复杂。《诗庄严论》中的修辞格有39种,此后不断充实和发展,达到100多种。追求藻饰是古典梵语和藏语“大诗”的普遍特点,而其中的极端者,则以雕琢繁缛的文体和艰难奇巧的修辞为诗才,甚至近乎文字游戏。这样的文学作品自然不能再像吠陀和史诗那样依靠口头创作和传播,而必须依赖文字和书写。(51)史诗虽然也有书面文本,有抄本、刻本、提词本、转述本等多种书面文本样式,有“精校本”、“权威本”等概念,有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及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等划分,(52)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口头传统,在口头进行创编、演述、流布,就同一个故事而言,每一次演述,都是一个不同的文本,都是一次现场“创编”,(53)差异性和流动性是其主要特征。对“大诗”的研究,我们从固定的书面文本入手即可,但对于史诗研究而言,“艺人、文本和语境是它的全部要素”,(54)系统研究这三个方面才有可能完全把握作为口头传统的史诗。因此,书面性和口头性是两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区别。
口头文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文本间的互涉关联。“在富于种种变化的方式中,一首置于传统中的歌是独立的,然而又不能与其他的歌分离开来”,(55)即史诗具体的演述文本与口头传统具有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说明史诗文本并不是歌者真正独创的,而是在多种文本的延续和差异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大诗”的题材大多取自史诗,但它不能作为史诗口头传统的一部分,不像史诗与其他口头叙事文类的关系一样有彼此重合、叠加、互渗、合并的关系,而只能是基于口头传统而创作的书面文本叙事,是以史诗为基础的新的个人话语实践。
其次,叙事文本的长度方面,尽管“大诗”也要求有若干章节的长度,个别古典梵语和藏语“大诗”篇幅不短,但总体上来说,“大诗”的篇幅远远不及史诗。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是集多种民间口传文化为一体的超级故事。例如,“《格萨尔》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是人类口头艺术的杰出代表。”(56)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史诗范本均是鸿篇巨制,而“大诗”只是故事取材于史诗某一个片段或若干章节的诗人作品,相对于史诗的“原生性”来说,它们是“次生的”,相对于史诗的“完整性”来说,它们是“片段性”的。“大诗”的理论本身就提出,为了不让听众感到厌烦,不能太短,但也不能太长,适中的长度有助于“大诗”长久流传。史诗叙事宏大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它不像“大诗”一样是一个作者个人诗艺和技法的展现,而是源远流长的民族集体口头传统中创编、演述、流布下来的,是与民族的历史一起成长的宏伟叙事,记载了一个民族关于天地形成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以及事关民族命运的战争和英雄业绩,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达,被称为“复合文类”、“超级文类”、“重大文类”,从中划分出了许多种亚类。
第三,叙事法则和叙事要素方面,“大诗”创作在主题、人物、空间、情节诸层面有传统既定的“标准”,并且需要充满味和修辞。这既是“大诗”创作的叙事要素,也是“大诗”叙事的基本法则。对史诗程式化特征的全面发掘和研究,肇始于口头程式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从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三个结构性单元,对史诗的程式句法、程式频密度、特性修饰语、歩格、平行式、跨行,以及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进行研究,指出口头程式是歌者得以创编和演述鸿篇巨制的根本所在。因此,“大诗”的书面创作规制和史诗的口头程式特征是两者的又一重要区别。
文类概念的界定和文类范畴的划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是对一种文类或特定文类所属作品的属性问题进行讨论的前提所在。只有通过对文类概念和范畴进行具体的阐述和划分,对文类特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和分析,我们才能对某种文类的本质特征和文类之间的边界产生较为清晰的认识,也能基于这项工作而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大诗”和史诗的相似性体现于外在的文本长度和叙事结构上,而差异性则聚焦于内在的文本形成和作者身份等层面,这种表明上的相似性和本质上的差异性,体现了两种文类各自所秉持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特征:书面性和口头性。这一点,不仅与文本的构型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以文本为中心的生产者、接受者、接受语境息息相关,而这些正是我们探讨文类范畴和概念边界的关键要素。
作者简介:吉多加,男,藏族,青海同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4年第1期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