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是畲族人生仪礼得以记录的三种不同媒介,而三者间的交互指涉关系不仅在互仿、互释及互补的叙事过程中,较为完整地描述了传统人生仪礼的历史面貌,更在仪式实践的展演中对接了现实生活。长联作为畲族人生仪礼的视觉表达模式,生发于盘瓠神话的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传播。“古老”对长联知识的夹叙,既为图像观想的仪式实践提供了基础,又为客观解读图像奠定了框架内叙事的前提。总之,人生仪礼的多维度叙事需在其共享者所能理解的知识范畴内发挥功能。
关键词:人生仪礼 口头传统 图像叙事 《高皇歌》 祖图长联 交互指涉
不同族群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根据不同需要,于个体人的重要成长环节设定具有显著仪式性的行为规范。这种被称为“人生仪礼”的历时性生命节点,不仅折射出个体人的生物性变化,也是对其社会身份的集体赋予和个体人格的文化塑造。对某些族群的个体成员来说,只有逐次经历这些先期设定的特殊“考验”,方能从事某些个体行为或参与某些集体活动。因此,人生礼仪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而其“与社会组织、信仰、生产与生活经验等多方面的民俗文化”的交织,“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民俗文化类型中的生命周期观和生命价值观”。同其他民俗事象一样,人生仪礼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形式或内涵的变异,但要维系这种行为规范的有序传承,除了身势语的代际承袭,某些族群还会在口头传统之外,采取文字记载或图像描绘等手段加以记录,从而在族群成员的言行举止中,形成某种具有典型传统指涉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作为神话人物“盘瓠”生平的记述方式,不论是《高皇歌》,还是祖图长联,都是畲族民众记录本民族人生仪礼的直接反映。为了进一步阐述以上现象在畲民社会的具体表现,笔者将以浙江省云和垟县坪岗蓝氏《高皇歌》及其与该宗支所藏祖图长联的交互指涉关系为例加以说明。
一、口述、文字及图像:人生仪礼的三种记录方式
畲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现有学术成果表明,在畲汉两大人们共同体尚未普遍接触的隋唐之前,以“畲”为主体的古代族群,通常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并传递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此后,特别是“潮”(隋)、“漳”(唐)二州府的接续设立,不仅增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南边区的统治与管理,也为畲汉两大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交流创设了条件,而随着中原汉民地不断南迁,这种交流变得更加广泛。虽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以“客家”“福佬”为代表的汉民支系中,发现畲族文化元素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畲汉文化在封建社会就是彼此对等的,相反,强势的汉文化在不断改变畲族先民之生活习俗的同时,也因某些切实利益的争夺而产生影响深远的族际矛盾。不过,从积极的一面讲,畲族先民对汉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和改造),尤其是对“汉字”的习得,直接促进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族内传承和族外传播。此外,虽从现有历史遗存中我们很难确定畲族先民是否在隋唐之前既已创制出属于本民族的绘画传统,但可以肯定地说,现已发现的以描绘盘瓠生平为核心的祖图长联,却显露出典型的汉民文人叙事画的特征。
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畲民社会的口头传统,盘瓠神话承载了很多来自远古的族源信息。虽然散文体盘瓠神话在畲民日常生活中并非随时都可明言的族群记忆,但相较于韵文体史诗《高皇歌》,其神圣性俨然较低。换言之,作为演述盘瓠生平的另一种口传艺术,史诗《高皇歌》有着更为严格的语境要求。并非所有以“盘瓠”为核心母题的神话文本都完整呈现了盘瓠的一生,但现已发现的畲族民间刻/抄本和现代整理/出版本表明,这些具有显著“格式化”倾向的“作品”,大都全面演述了盘瓠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与神话文本的制作一致,《高皇歌》对盘瓠生平的演述则表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样态——相较于篇幅有限的神话文本,史诗在表述同一被叙对象时,并未由于严格的格律要求而在内容上有所减损。此外,基于口头程式的史诗创编与流布,不仅反映了演述者对族群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调动能力,也不断丰富着史诗文本的诗行长度、内容广度及意涵深度。不过,与同样具有“盘瓠”母题的瑶族史诗《盘王大歌》不同,《高皇歌》除了起头的“创世”与歌尾的“迁徙”,并未产生超越“生平”的信息,因而其叙事内容不仅简洁、直接,且篇幅较短。现有调查表明,垟浙江省云和县坪岗畲民蓝观海演述的《高皇歌》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史诗文本——共124.5条(4句1条),498句(7字1句),3486字。
如何通过艺术手法或仪礼程序呈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一项十分繁杂且具地方差异的集体行为模式。然而,现有文献和调查显示,历时性的过程切分及其顺时性的仪礼接续,不仅是一种较为简易的表现手法,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就中国来说,从汉文典籍中的“三礼”、明清以来的地方志或文人笔记,乃至部分民间宗谱,都将个人的某个年龄节点视为人生进程的重要标志,从而形成以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寿诞(生日)以及丧葬礼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脉络,而部分族群还于其间穿插或嫁接了入社、入教等颇具宗教性的仪礼活动。虽然由“节点”串联而成的生命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经历,甚至某些影响个体发展的重大事件,但作为一种记录方式,这类通过仪礼却能清晰标示出个体人的成长路径,因此是符合集体记忆的习俗惯制。对特定族群而言,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并非一蹴而就的集体需要,而为了将系统化的仪礼行为有序传承于后人,记录方式的可见与不可见则成为两种彼此依存的生活方式。对无文字民族来说,除了身势语的视觉可见性,艺术化的言语表达则从听觉的不可见角度,为人生仪礼的代际延续提供了有效途径。在畲民社会,以“盘瓠”为母题的口头传统,特别是史诗《高皇歌》,其所演述的核心内容恰是以盘瓠所经历的五大人生仪礼: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入教礼→丧葬礼为基础,从而在五个叙事单元的顺序组合中完整叙述了盘瓠的个体生命史。
虽然人们无从定位盘瓠神话与史诗《高皇歌》的出现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口传艺术是于代际更迭中逐步完善的叙事表达模式。在大多数浙南畲民看来,描绘盘瓠生平的祖图长联是晚出于神话与史诗的集体创造。畲民蓝陈启曾言:“敕木山村人都说这个祖图是根据我们这个‘高皇歌’画的”;畲民钟财兴认为:“这个图就是根据‘高皇歌’绘的了,‘高皇歌’就是唱这个图的,内容是差不多的了”;畲民雷长江根据“老辈人这么传下来”的说法指出:“先有的故事,后有的歌,最后才有的祖图长联”。畲族学者雷光振则更理性地分析道:“口头表达的东西在前,绘画的东西在后了。因为很多历史事实表明,在远古时期,语言就是人们传递文化知识最主要的手段,而象形的图案、文字等都是后来才有的,更不用说是绘画了。所以我认为是先有口头的盘瓠神话,才有的祖图长联。”由此可见,在浙南畲民的知识体系中,祖图长联是根据史诗《高皇歌》等表现盘瓠生平的口头传统绘制而成的一种仪式法器。对此,笔者深以为然,但需加补充的是,作为一种故事画,祖图长联不仅体现了文人画的时代印记,更突显了汉民信仰——陈十四(闾山)崇拜——在畲民社会的深远影响。既然祖图长联是以《高皇歌》等口头传统为蓝本绘制的,那么其理所当然地无法跳出这些口头传统所限定的五大人生仪礼。的确,不论是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井头坞钟氏长联,还是本文引以为证垟的坪岗蓝氏长联,莫不如此。只不过,对同一对象的表述,言语和图像所呈现的叙事内容并不具有一一对应性,而这恰恰突显了两种记录模式在听觉与视觉上的差异。
此外,一个十分显著的社会现象在田野调查中得以突显——在浙南畲民聚居区,保有祖图长联的畲民群体,同时也有于相关仪式活动或日常生活演述史诗《高皇歌》或其变体(如《兵歌》《思念祖宗》等)的惯习,甚至拥有数量不等的《高皇歌》手抄本或嵌入宗谱“序”的盘瓠神话,但能演述以上口头传统或保有相关书写文本的畲民群体并不一定保有祖图长联。换言之,以盘瓠生平为表现核心的口头传统并不依赖于祖图长联而可单独存在,相反祖图长联却因口头传统的实际演述而更具文化传播力和解释力。据此可知,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是畲民针对同一信仰对象而创设的三种人物生平表述模式。媒介虽有不同,且均能独发挥文化传承的实用功能,但这并不影响言语、文字及图像对集体记忆甚至实际行为的同一性记录。而三者间的互仿、互释及互补,不仅丰富了族群文化的表现样态,更深化了族群成员对同一被叙对象的认知与理解。
二、“语”“文”“图”的交互指涉:人生仪礼的叙事表现
言语是线性表述的时间流,它通过己方之口传入彼方之耳,并在输送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中产生较为一致的大脑图示,否则便会出现“词不达意”或“问官答花”的后果。图像的空间性为观者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视觉体验,但这种来源相对单一的形象认知过程,不仅难以还原图像本身的历史信息,还可能在去语境化的影响中呈现更为多样的歧义性解读。正所谓“可见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并非它的原本如此的样子,而是被我们的视觉结构选择、强化、改造了的结果”。尽管“对叙事作品的研究不受媒介的局限,因为文字、电影、芭蕾舞、叙事性的绘画等不同媒介可以叙述出同样的故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语”“文”及“图”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特别是在表述同一对象时,三者之间的互仿、互释及互补既能丰富彼此的叙事内容,又可深化被叙对象的文化意涵。正如赵宪章等人所言:“‘诗画一律’是语言和图像在心理层面上的合体状态,‘书画一律’则是语图在物理层面的合体表现。”据此可知,呈现同一被叙对象的“语”“文”及“图”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一定的一体化特征,而这一特征反映在普通大众的生活实践上,就是一种不需特别明言的“交互指涉”(cross-referencing)关系或“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
“交互指涉”是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Nagy)于《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涉及的重要术语,而“传统指涉性”则是约翰·M.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内在艺术》(Immanent Art:From Structureto Meaningin Oral Traditional Epic)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巴莫曲布嫫在引介二词时认为:“从英雄诗系,到两部荷马史诗,再到各种城邦版的荷马史诗,这些文本之间是互有关涉的,取决于叙事传统的渐进演成和构合。有些典型的史诗叙事片段还出现在壁画和瓶画上,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异。所以,纳吉提出了‘交互指涉’这个概念,并指出应当从一种历时性的观察出发,去理解史诗传统,从一个吟诵片段到另一个吟诵片段之间的任何一种交互指涉都当视作传统。在弗里那里则被概括为‘传统的指涉性’,跟纳吉的概念可谓异曲同工。”由此可见,不论是“交互指涉”还是“传统指涉性”,都是在“历史性”的维度中勘察“文本和文本之间,或者演述事件和演述事件之间,或者演述人和演述人之间,甚至文类与文类之间”的叙事传统——这不仅是经常复现于日常生活的集体认知或行为,也是约定俗成且不言自明的客观实在。就此而论,以盘瓠生平为表现核心的《高皇歌》(盘瓠神话)与祖图长联,其叙事关系正是传统指涉性的典型反映。
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入教礼以及丧葬礼是构成盘瓠生平的基本环节,是《高皇歌》、宗谱“序”及祖图长联重点演述、记载及描绘的情节。那么,三者之间的交互指涉关系究竟如何呈现,这又折射出怎样的文化认识观,则是下文将要集中论述的内容。
在畲民社会,虽然以“盘瓠”为核心母题的叙事文本十分多样,但通过 母题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口头演述(散文体和韵文体)、文字记载(宗谱“序”和相关手抄本),还是图像描绘(祖图长联),盘瓠神话的元叙事结构大致可分为七个情节,即盘瓠神话=三皇五帝+盘瓠出生+平番受封+变身娶妻+移居凤凰山+打猎殉身+族群迁移,而这些叙事单元又可细化出数量不等的次级母题(表1)。

从这一母题链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处于一级母题的元叙事单元,都可以是一个由不同细节构成的独立事件。由此可知,每个元叙事单位都有其始末和因果,是可以单列为一个叙事片段的集体创作。不过,每一个元叙事单元的内部虽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的艺术表达,但这并不代表元叙事之间不具备起承转合、相互勾连的伏笔关系。如“平番受封”中的“高辛张榜”与“盘瓠揭榜”使“变身娶妻”得以实现,甚至成为后续故事有序演进的基础,而“上山打猎”则直接引发了“做功德”与“安葬凤凰山”的叙事内容。从更大的叙事结构看,没有“盘瓠出生”,就没有“平番受封”,更谈不上“族群迁徙”等表现族群壮大,且又彼此凝聚的认同话语。在两级母题的顺序加成中,可以轻易发现盘瓠神话的基本叙事结构及其表现手法,而单一母题的罗列则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人生节点和叙事情节的对应规则,特别是“盘瓠出生”“变身娶妻”及“打猎殉身”等元叙事,直接标示了“诞生礼”“婚礼”及“丧葬礼”,而“移居凤凰山”下的二级母题“闾山学法”则突显了道教闾山派对畲民社会的重要影响,因而隐含了“入教礼”的存在。
虽然我们无法从字面意思定位畲族“成年礼”在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述中的位置,但从人生仪礼的发展脉络来看,其一般位于“诞生礼”与“婚礼”之间。因此,就“语”“文”及“图”交互指涉关系中的畲族“成年礼”而言,必然要从“平番受封”这一元叙事环节中探寻。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可以把“平番受封”这一历险式过程视为一种生命考验,其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一场持久战的胜利,更在于受考验者之社会身份的彻底转变——成为一个为所在族群认可的“人”。虽然有学者极力考证盘瓠及其所平之“番”(或“戎”)的真实性,但这依然无法从根本上确定这一源出口述记忆的“事件”是否不容怀疑。当我们将视角置于人生仪礼的生活表现上,就能发现,这场令高辛帝及其臣民难以完成的平叛任务,或许只是一场针对族群个体的成长“试炼”,且其对象则是与本部落有着敌对关系的另一族群。而从盘瓠所取得的胜利来看,这一成果似乎还隐含着较为原始的“猎头”因素。只不过,在历时的发展中,这种讲述被不断改变,并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上升到家国天下的英雄主义层面,成为一种既与主流意识相统一,又保持相对独立族性的集体话语。有学者指出:“在原始的成年仪式特别是男子成年礼中,要集中完成一系列规定的体能训练和受到相当痛苦的身心折磨”,而采用的方法或手段主要有:
1.环境的突然改变,十几岁的年轻人要被带往远离父母与亲人的陌生地方;2.置身于人为的艰苦生活当中,饮食、睡眠、说笑行为等受到严格限制;3.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与耐力培养,如进行长距离行军等;4.接受鞭打等肉体痛苦和施行损伤性手术如割礼、文身、凿齿等;5.制造恐怖场面,使年轻人受到惊吓。
由此可见,盘瓠的“平番受封”俨然具有“1”和“3”的考验性。有学者指出,成年礼的意义是“使那些将承担社会责任的年轻人得到身心磨炼,从而具有迎接未来艰苦生活的能力,但从情绪感受的监督来看,年轻人在仪式中所遭受的痛苦越大,就越会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社会地位正发生急剧变化,同时加强他与现场周围人的连带感”。不过,对很多族群来说,考验的结束并不一定代表整个成年仪礼的结束。换言之,“成年礼最终要使经过严格考验和训练的年轻人拥有正式社会成员的标志,如改变发式和服饰、佩戴特殊装饰品、文身与凿齿等身体变形,新命的名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也是表明年轻人身份发生变化的寻常标记”。据此反观盘瓠神话及其图像表达,即可发现“平番受封”并非“历练”的结束,位处“变身娶妻”中的“金钟变身”才是这一过程的终点,其标志则是“人身”的形态之变与“头饰”的获得。而畲民对这种男性“头饰”的解读显然突出了“成年”以“入社”的习俗惯制,即被公认为“盘瓠集团”的一员。其实,暗含“室”之“禁忌”的“金钟变身”之所以会和婚礼杂糅,很可能是对“成年礼”逐渐融入“婚礼”的过程性反映,而前置的“张榜”情节也为此做了铺垫。尽管以“三礼”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历代皆受推崇,但明清以来的地方志显示,针对“成年礼”的表述不是被“废”,就是为“婚礼”取代,甚至不予记载。因此,隋唐以来深受汉民宗族文化影响的畲族民众,势必会对本民族人生仪礼做出一定修改,以便适应日益频繁的畲汉交流,而口头传统与图像叙事则为这种变迁留下了痕迹。据此,我们可以把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中的畲族人生仪礼与盘瓠神话的元叙事对应关系表述为“表1”。
盘瓠神话的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具有典型的传统指涉性,而图像描绘的创作过程有赖于“一般性顷间”的顺序排列。不过,言语和图像本就属于两种不同的传播媒介,因此二者之间也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的交互指涉,所以彼此间的互补也就在所难免,但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盘瓠神话的多样性。虽然现已发现的祖图长联超过了八十幅,但其类型却极其有限。如果从“内部构合形式”的角度予以划分,祖图长联可有以下四种类型,即“分格漫画式”“接续连环式”“图册分页式”以及“壁画式”。除“壁画式”外,其他三类长联均由超过30帧(甚至达到70余帧)的一般性叙事垟顷间构成。我们已经知道,坪岗蓝氏长联的一般性叙事顷间共有39帧(不含题记),而由蓝观海演述的《高皇歌》则有498个诗行。通过“语”“文”及“图”的内容比照,我们可以把蓝氏长联的39帧一般性叙事顷间与《高皇歌》的498个诗行,同盘瓠神话的元叙事单元及其所对应的人生仪礼梳理为表1所示的内容。
通过表1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坪岗蓝氏长联在描绘五大人生仪礼时,所使用的一般性叙事顷间并不具有数量上的一致性,且呈现出一定的“M”型布列格局。与此相似,由畲民蓝观海演述的《高皇歌》在叙述五大人生仪礼的发生过程上,其相应的诗行安排也呈现出明显的行数差异,并表现为一种类似“W”型的演述模式。不过,在顷间序列的帧数与史诗诗行的行数之间,并未体现出直观的反相关(或反比例)关系,即诗行行数的多少并不能严格限定顷间帧数的多少。因而每组顷间帧数与诗行行数的比例关系不仅没有相互接近,更不恒定。换言之,面对同一被叙对象,图像叙事与口头传统很难走向平衡。不过,尽管每帧叙事顷间在整幅图像上所占据的画幅大小各不相同,但由多帧叙事顷间构成的一段叙事情节,根本无法超越这段叙事所对应的诗行行数。更重要的是,史诗所能言说的内容并不一定能切实反映在图像的描绘中,如用24个诗行(287—310)加以演述的“闾山学垟法”,即“入教礼”环节,在坪岗蓝氏长联上仅被描绘为两个连续的一般性叙事顷间。而这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所有长联中有关“入教礼”描绘的顷间数最多的一幅,也是画面动感最强的一幅,其他以单顷间表现的长联则多呈现“△”的静态人像排列模式。另外,还有将数个叙事情节并列于同一叙事顷间的现象,如位处“打猎殉身”中的“山羊触死”“尸悬于树”及“族人寻找”等,则被统一描绘于顷间序列33,而这帧图像所对应的诗行却只有6句42字。
图像叙事作为一种空间叙事,其所承载的内容相对有限——这不仅在于画幅大小,还仰赖绘制者对叙事中“动作”的“语象”把握及其“物象”转化的能力。相比之下,口头传统则是时间叙事,它并不受限于篇幅长短,而“程式”语法则为史诗篇幅的不断拉长带来可能。针对这些重复性语词或段落,图像绘制者一般不会刻意再现前一帧叙事顷间的内容,相反还会将某些连续发生的“事件”加以并置,从而导致“语”“图”叙事的不对等——直观的图像并不能完整复现抽象的言语。
如果仅从图像叙事或口头传统的单向度考察,不论祖图长联的“M”型布列格局,还是史诗《高皇歌》的“W”型演述模式,都表现出起伏有序的音乐特征,而这种叙事现象的代际传承不仅是长久积淀的结果,也是集体选择的重要表征。通过表1所呈现的交互指涉关系,我们可对五大人生仪礼的图像描绘做出(帧数)降序排列——成年礼—丧葬礼—婚礼—诞生礼—入教礼,而其在口头演述中的(行数)降序则可表述为:成年礼—丧葬礼—婚礼—诞生礼—入教礼。因“诞生礼”和“入教礼”所用诗行等同,所以二者的位序可以互换。尽管顷间序列与史诗诗行并不具备直接反相关关系,但在人生仪礼的排序上却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而这正体现了畲民的普遍认知——图像叙事源自口头传统。然而,这种排序并不代表人生仪礼在畲民社会的重要性也是如此。任何一种人生仪礼的实际“操演”都是集体对个体的阶段性族群认同与身份强化,因而并不存在等级秩序的客观差异。只不过,对“平番受封”与“打猎殉身”的大篇(尺)幅演述和描绘,则反映了畲族民众对“忠勇”精神的崇尚与坚守。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人生仪礼的社会适应性逐渐降低,从而淡出人们的现实生活或为其他仪礼所“吞噬”。这会否影响其在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中的丰富程度,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如本文所涉及的“成年礼”和“婚礼”,并未由于前者的后者融入,而削减前者在“语”“文”及“图”中的复杂表现,相反后者的被叙情节则略显简单。
上文之述指出,作为记录人生仪礼并使之有序传承的重要媒介,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不仅较为全面地复现了远古先民不同凡响的生命历程,还在后世的族际交流中,维系着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忠勇。虽然三种媒介的记录能力各有短长,但对同一被叙对象的细节展示,却在交互指涉关系的连接中更趋完整。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对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的互仿、互释及互补的探查,更为深入地发掘特定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族群“表达文化之根”。
三、观想:“语”“文”“图”交互的“古老”媒介
人生仪礼的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是畲民社会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记录方式,这种普遍存在的集体创造,也因族群迁徙与族际交流而产生部分细节的地域差异,但这并不影响“畲”民族基于盘瓠神话而形成的认同意识。相较于日常生活中较易获得的口头传统和文字文本,图像叙事的非日常性则限定了族群成员直接获取视觉体验的语境。也就是说,图像叙事的隐秘性要远远高于口头演述和文字记载的公开性,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祖图长联是为其保管者秘密珍藏的物质存在。此外,口头演述与文字记载(哪怕部分宗谱)还具有较强的个体属性,但以祖图长联为代表的图像叙事不仅为集体所有,且很难脱离具体仪式——祭祖、传师学师及做功德——而独立发挥其所拥有的社会功能。故而,普通畲民欲从日常生活中获取有关祖图长联的信息,除了查阅相关文献外,只能寄希望于掌握相关知识的族群精英。与当代社会相比,近现代及之前的畲民识字率相对较低,因而口头传统也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较之于史诗《高皇歌》对演述语境的严格要求,“古老”则相对宽松,而实地调查指出,后者较之前者会穿插更多有关祖图长联的本体知识。
“语”“文”及“图”的交互指涉关系不仅是“语象”和“物象”的实体表征,更是一种深入人之意识的多维度认知反映。因此,“古老”演述之于听觉感知可说是“仪式”实践之于视觉体验的先决条件之一,而这恰是三种叙事媒介之所以形成“交互指涉”的基本要素。固然“古老”所附带的长联知识是点状的、零散的,但这并不影响畲民个体对它的接受。对于这种被称之为“自然而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生活经验。在外来者看来,也许就是地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教育”过程,正是这种“不经意间”获得的“耳闻”知识,却能在“目睹”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眼”与“耳”的完美对接。正如钟小波所言:“我们这里没有专门讲祖图的人,一般也不会有人去问,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大家自己去看,自然也就会了。这都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事,根本没那个必要……我们不管是做功德,还是传师学师,看到那些祖图就能很自然地联想到我们听过的那些故事。”据此可说,那些为大众约定俗成的民间图像,自有其固定的所指与能指,它不需要刻意讲述,但其享用者已然在日常生活中分享了有关它的经验,只是这种产生于日常生活的交流方式,并不为大众所特别留意。不过,这种“雁过留声”式的经历已然于集体无意识中,注入个体的知识系统,从而为代际传递构筑起可以互通有无的桥梁。
那么“听觉”与“视觉”的实践融合是如何发生的?钟小波的口述似乎已经给出答案——“自然地联想”。笔者认为,耳之于“听觉”体现的是一种抽象概念,眼之于“视觉”反映的是一种直观物象,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感官体验,而是基于人体机能的有机统一体。尽管西方学界长期存在提高“听觉”地位以打破“视觉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斯(WolfgangWells)所言:“高扬听觉并不意味未来人们只消使用耳朵,相反它是指世界在微观物理上早已是由震荡组成,指某种隐藏的声学被刻写进我们的思想和逻辑之中,指我们对他人和世界的行为在总体上更应当专心致志,兼收并蓄。视觉和听觉的纯粹感性意义总是伴随着意味深长的意义。”由此可见,对他人与世界的认识,需要在视觉与听觉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发挥最大功效。不过,视觉与听觉并非人们认知世界的全部感官,而触觉、味觉及嗅觉等无一不具有认知功能。可以说,人之五官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先后顺序。但正如上文所言,祖图并非日常生活的展示品,而是日常之非常时段的仪式用具。因此,相较于“视觉”的直观体验,“听觉”的抽象感知似乎来得更为超前。换言之,“古老”在畲民眼观长联前,似有更为强烈的先验性。
其实,我们并不能将“眼”认知图像叙事的过程视为一种简单的“看”。由于人们要将先验的听觉经验有机地结合于视觉实践,而“自然地联想”在充当“听觉”与“视觉”的中介时,则突显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对此,美国艺术史家巫鸿称之为“观想”。巫鸿在研究古代佛教讲经、经变及经变画的关系时指出:
虽然讲经和经变在神学基础和引导方法上是并行的,但与经变画,尤其是与阿弥陀壁画直接相关的宗教礼仪并不是讲经,而是观想……这里“观”一词指禅定过程,通常以信徒集中意志观想一幅或者一个雕像开始,修习用“心眼”看到佛和菩萨的真形……换言之,礼拜者需要通过禅定在幻想中构造出沐浴在佛光中的净土世界及其中的无限神灵和情境……的确,“表现”一词经常被错误地运用到对这些绘画的讨论之中,因为在神学层面上,一个人工制作的画像是绝对不可能表现真正的佛和净土的——佛和净土只能存在于信徒的心念之中。读善导的著述,我们可以明白这些绘画不被认为是创造性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是起到刺激禅定和观想以重现净土世界的功能。善导因此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见”:一种是“粗见”,与眼睛和想象力的能力与活动相连,另一种是“心眼”,只有当后者打开才能真正认识到净土世界的美妙。
对长联的“观想”并不同于佛教徒对“净土世界”的幻想,但两者的前提条件似有相通之处:“观”经变画的佛教徒需在善导著作的引领下进入禅定境界,并经由“粗见”到“心眼”的转变才能真正体认净土世界的存在;而“观”长联的畲民则是在先验的“古老”接受中,进入仪式所设定的神圣场域,但他们是否会发生由“粗看”到“心眼”的转变,则有赖于他们对“祖居地——凤凰山”的想象力和认知度。或许,我们可以把“观想”之“想”视作一种发自内心的感知过程,即将先验的听“古”经验从记忆中析出,并将之对应于视觉所观的对象之中,从而形成言语文本的物象转译,进而深化个体对物象的记忆。
画家刘继潮指出:“中国古典绘画之‘观’是事物自然存在呈现的境界,没有预设前提,是‘观的观点’。‘观’是综合经验的直觉体验,是记忆、想象的创造,而不选择单一再现视网膜成像的路径……故而能自由地展现一个包含一切的整体的动态的创造过程。”虽然这种理解主要针对于文人绘画的成像依据,但如果没有对既成图像的“回观”,又何以觉察成像的思维过程。而这种“蕴含生活经验、历史积淀、审美体验,回避科学原理、重视人文情怀,不画直接的视觉所见,画贮存的意象和视觉经验”的“本体之‘观’”,“造就了中国古典绘画独特的体系、理路、方法与语言形式”。其实,不论是绘图还是观图,人们都将处于一种特殊的感知状态——游观——中。所谓“游,是身体挪移运动的行为;观,是心性综合直觉的感悟与体知”,因此“游观是人的本体之观,与宇宙本体的物象之原,神遇而迹化,融合无间,天人合一式的体验路径。游观的本体之心贮存是物象之原比例、原结构,是有机的、整体的、连续的意象结构图式”,而“正是‘游观’的本体规定生成了中国古典绘画长卷与立轴的独特形式”。据此而论,当包括畲族民众在内的所有长联观看者,于特定语境“欣赏”长联时,既已处于“观想”状态。他们会利用自己所储存的一切有关祖图的“古老”信息,在画面从右向左或从上到下的展放中,“游观”于图像所模仿的言语叙事,从而在巩固自我记忆的同时,加深了个体对长联内蕴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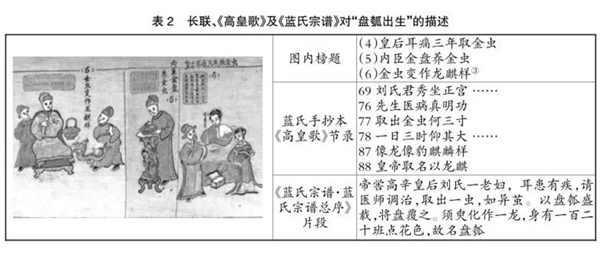
正如表2所示,当观者视野游走于长联所描绘的“盘瓠出生”时,便会不自觉地调动自己所积累的史诗或神话文本,从而在交互指涉的联想中,较为完整地复现这一集体记忆,甚至能将之对接于真实的诞生过程——求子([夜饮星坠])→孕育(耳疾取茧)→庆生(化龙赐名)。
概言之,“古老”的零散性并不能阻碍广大畲民对长联知识的仪式实践,而畲民在自我熔炼中逐步系统化的长联知识,虽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或丰富或简洁,或清晰或模糊,但它们却直接反映了区域民族共通的地方性知识。从观看图像的层面讲,展放长联的过程就是讲述图像内故事的过程。人们通过“观看”图像,将内化于记忆的“古老”直接对应于视网膜成像的过程,则是“自然地联想”言语叙事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言,不论是“听”还是“观”,图像叙事的民间发生都具有明显的“自然”性。进一步讲,畲民对图像叙事的认知过程,实是一种对约定俗成的生活文化的接受过程,而这种过程不需要刻意言说,但需要躬身实行。
四、框架内叙事:图像解读的口头复现及其演述规则
由于民间图像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尤在仪式中),因此当“观想”成为回溯图像所再模仿的言语叙事时,民间图像于人们口头的再演述,无可置疑地将因既定的先验预设——来自“古老”的地方性知识——呈现出一种“框架内叙事”的倾向。换言之,再模仿于口头传统的图像作品,在“观想”的情境中复现于人们的口头时,其依然要遵循民间约定俗成的演述规则,甚至不能随意脱出口头传统所既定的“原型”范畴,从而避免给听众(族群成员)带来理解上的歧义。
笔者虽然无法确定历史上的畲民是否存在“看图讲故事”的情形,但上文所引口述材料已然表明,在当代畲民的记忆中是不存在“看图讲故事”的。在2017年5月15日的一次访谈中,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四位老师(吴晓东、王宪昭、毛巧辉以及周翔)和笔者之请,钟小波在师公钟雷根与钟益长的陪同下,以其2016年摹绘而成的祖图长联为例,向我们演述了他所掌握的盘瓠神话。在这次演述中,钟小波不仅可以借助《高皇歌》的开头:“盘古开天到如今,世上人何几样心”,“一朝江水一朝鱼,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内容概述长联中的三皇五帝,更重要的是,他在依据长联画面演述盘瓠神话的同时,既详细解读了部分画面的内容,如“娄宿下凡”“番王酒醉”“观礼七贤洞”等,又将部分画面所对应的现实生活娓娓道来,如“婚礼”“传师学师”“做功德”以及“男耕女织”等,但不论他如何讲述,得到钟雷根与钟益长认可的盘瓠神话,都未脱离笔者所构拟的神话“原型”。不过,这一“不算自然”的演述活动依然让我们感受到:没有长联依托的神话演述,很多图像细节及其与现实生活的交互指涉关系则很难呈现。细言之,长联的“在场”不仅能让神话本身所具有的叙事内容,随着图像的左右移动,得以较为完整的演述;某些画面虽然简单却内容丰富且能直接对应于现实生活的叙事顷间,则会在演述者的发挥中得到更精彩的解读。据此笔者认为,图像对人之记忆的发掘或引导具有极大的催化功能。
就像隐含“入教礼”的“闾山学法”一样,除坪垟岗蓝氏长联用了两帧颇具动感的叙事顷间加以描绘外(表3),其在大部分长联中的表现都是单一叙事顷间,且均为静态的人物肖像,但这并不影响畲民(特别是师公)据此演述出更为丰富的故事情节,如“过九重山”“许真君传法”“智斗山鬼”等,甚至包括“传师学师”的仪式环节及其与“陈十四信仰”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在史诗演述与接受的互动模式中,作为物质文化的语义性知识体系——相关史诗诗行已经以隐含文本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大脑中。同时,无论是作为散体讲述的史诗知识,还是在仪式中演述的史诗知识,都能与物质文化实现互证、提升和强化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整个史诗传统的表现力、感染力和记忆力。物质文化与口头史诗不是分道扬镳,而是结构化地联袂出演,是整个史诗传统的有机部件。”据此笔者认为,虽然无法否认口头传统在个体演述活动中会产生一定的变异现象,但这种变异并非随性而来的自主行为。正如上文所言,任何一则言语叙事都必须在民间约定俗成的规则中加以演述,而这一规则当然也包括叙事内容。不过,正如刘魁立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所提出的“情节基干”一样,人们对特定图像的接受,以及因对之的(故事化)再演述(解说)也是在“情节基干”的基础上生发了异文。这些异文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主体内容依然未变。然而,一旦这种演述脱离大众所能理解或接受的范畴,这种变异就会为大众所拒绝。
在2016年12月25日,即景宁县郑坑乡半岭村举办“传师学师”活动的第一日晚上,师公ZLF在仪式中途的“宴会”上,向在场十二位师公演述了他所认为“对”的盘瓠神话。可是,这则被众师公视为“政府编造”的故事并未讲完,甚至连高潮都未达到,即被在场师公们打断。事后,参与“宴会”的师公钟法标告诉笔者:“他(ZLF)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我们这里流传的故事,是他从县民宗局编的书里看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没有讲‘龙麒’的,都是讲‘龙□’,而且我们都说是高辛反悔不想把三公主嫁给‘龙□’,他非得说是三公主不愿意。我们祖婆是很开明的大家闺秀喽,不能这么讲的喽,所以就不让他往下讲了。”也许是受此影响,ZLF在第二日晚间应厦门大学师生之请讲解“狩猎图”时,就显得十分谨慎——他只说这幅图像反映的是其祖上的劳动场景,即“狩猎”活动,并指出这幅图也被绘制在长联之上,而正是这次打猎活动,让“龙麒”丧命于山羊之角,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做功德”。当笔者将同一幅图像的复制品拿给景宁县鹤溪镇东弄村师公蓝余根时,他不仅点明了这幅图像所绘乃“狩猎”场面,是畲民过去最普遍的一种生产方式,更进一步指出:“这个图要从上往下看,上面画的是打猎前要祭猎神,不祭猎神是不能去打猎的,是要触犯猎神的;下面画的才是打猎的场面。我们打猎回来,还是要谢猎神。猎神是很大的神,不能得罪的。我们做功德、传师的时候还要唱《猎神经》的。”由此可见,约定俗成的民间知识在个体试图冲破某些既定的习俗规范(即越轨)时,确有十分强劲的约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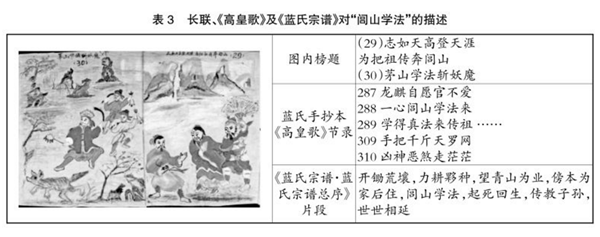
图像之所以能叙事,是再模仿于言语文本的结果。而异文众多的散文体盘瓠神话与韵文体《高皇歌》在成为祖图长联的再模仿对象时,也于畲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正如上文所论,图像本身的叙事模式自有其作为“物质”存在的特征,但图像叙事所呈现的言语交流模式,决定了图像叙事同作家文学一样,不仅存在于作品之内,也表现于作品之外。进一步讲,依据盘瓠神话与《高皇歌》绘制的祖图长联,其叙事时序必然难脱言语文本所设立的时间结构,而众多叙事顷间的秩序排列模式,同样要在传统的构图法则中,呈现言语文本所难以表现的叙事空间。对广大畲民而言,祖图长联并非日常生活的展示品,因而对其知识体系的个体把握,就需要在代际传递的口传心授以及特定仪式的躬身观察中获取,并于日常生活的个体熔炼中逐步系统化。虽然畲民个体所掌握的长联知识并不相同(甚至包含某些自我发挥的不合理成分),但这种存在于图像之外的个体记忆,却彰显了地方性知识在代际传承中的生命活力。然而,“讲古老”并非畲民获取长联知识的主体途径,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由于仪式活动的不定时性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层级性,掌握较多长联知识的师公群体也未必能及时解答相关人员的疑问,因而日常生活中的“讲古老”就为个体长联知识的获取提供了非主流途径。
作为“听觉”所赋予的零散知识,“古老”与仪式实践的“视觉”结合,则为长联知识的个体系统化提供了便利。当长联所再模仿的言语文本通过“观想”再次复现于畲民口头时,其必然要依据民间约定俗成的规则加以演述。换言之,根据长联演述的散文体盘瓠神话和韵文体史诗《高皇歌》必须在“原型”的框架内展现,否则将不会得到畲族民众的理解甚至接受。概言之,以不同叙事媒介记述的人生仪礼,在口述、文字及图像的“视”“听”交互中,实现了特定族群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而图像叙事的口头复现则离不开族群成员对相关叙事的原型把握。
结语
针对同一被叙对象的集体或个体认知,不同叙事媒介都能据其所长,为演述者、阅读者或观赏者提供属于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和叙事模式(或结构)。不过,叙事媒介的属性差异决定了它们无法彼此取代,从而难以一己之力全面呈现同一被叙对象的各个侧面。通过上文之述我们已经知道,作为口头演述和文字记载的盘瓠神话和史诗《高皇歌》以及图像描绘的祖图长联,分别从不同角度共同记录了畲族传统人生仪礼,而不可见的“听觉”感知与可见的“视觉”体验则在三种叙事媒介的互仿、互释及互补中,给予其创造者、享用者及传承者以更趋完整的“全官式”理解途径,进而为传统人生仪礼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约定俗成的言行规范。
以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为代表的叙事媒介,在表述同一被叙对象时,都会根据演述者、阅读者或观赏者的实际需要,产生符合历时性传承和共时性传播的多“官能”表述内容。也就是说,同一对象的被叙情节,或繁或简,或长或短,或精或粗,都掌握在个体手中,而这其中就包含来自个体对传统(集体)知识的积淀以及演述能力的合理发挥。然而,正如李杰所言:“文化是一种‘生活状态’,人的认知是被地域性文化和社会意识所塑造的。”据此笔者认为,大分散小聚居的畲族之所以会在历时性的发展中,于现实生活产生具有显著地域性的人生仪礼,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族群徙居他处后的在地化需要,但族群成员基于祖图长联的仪礼回溯却相对一致。这种反映个体认知对集体认知的习得行为,表现在观想祖图长联上,则是对盘瓠神话与史诗《高皇歌》的口头复现。纵然经由个体复现的故事情节有所差异,但不论详略皆未脱离既定的原型框架。笔者在上文讲到,有关图像叙事的口头复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表达,因而哪怕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中的每一次言语叙事,都是一则具有针对性的异文,而这些异文无疑都是生发于“基干情节”的这一次叙事。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位通过“古老”并经由仪式系统化长联知识的个体畲民,其每一次的观图实践都是这一次的对族群知识的强化过程,而每一次讲/听“古老”与参与仪式的过程也是这一次的接受、传播及认知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可以用于描述当事人如何处理事件,从中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经验,并用当事人的观点去诠释这些经验”。
总之,作为叙事媒介的口头演述、文字记载及图像描绘,在表现同一被叙对象时,能在特定族群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不需刻意言说的交互指涉关系。而这些源自世代相延的地方性知识,在成为新一代族群成员之内在认知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族群个体的自我熔炼,更需在集体认定的叙事框架中对图观想。因而,针对同一被叙对象的多媒介叙事,既是人们多角度呈现同一事象的有效手段,也是突破单一认知方式的重要途径。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