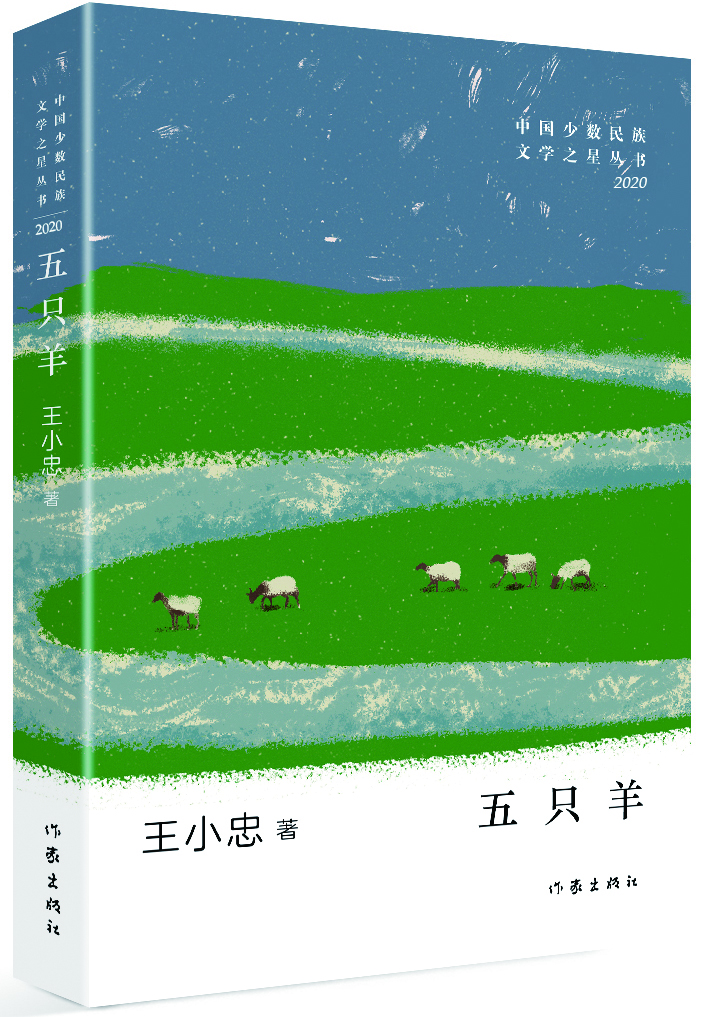
谈论自己的创作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作品既然问世了,作家就有一份责任谈谈自己的创作初衷。《五只羊》是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曾先后发表于《红豆》《青年文学》《湖南文学》《芳草》《广州文艺》《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等刊物。小说集以藏地甘南草原为背景,以当下农牧交汇地的生活为素材,试图集中反映藏、汉与农、牧两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交汇与反思。同时,对新时期以来,生活在甘南草原上的农牧民生活状态和思想变化给予尽量贴近的关注和描述。在这部集子里,倾注我心血最多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羊皮围裙》。
创作《羊皮围裙》的过程,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因为“银匠”作为藏区传统手工艺人,却正在逐渐消失。藏族是一个有着独特宗教信仰和生活审美的民族,在藏族人的观念中,各种银饰不仅是装饰品,而且是具有多重民俗文化含义的器物,在藏族人的生活中,“银匠”长期以来是一个重要而且受人尊重的职业。因此,这样的作品势必涉及大量行业内部的冷僻知识,好在我对这一部分生活并不陌生。为了创作这篇小说,我多次到郎木寺等地与目前尚存的为数不多的银匠们有过多次接触。我用“羊皮围裙”这个极富个人化色彩、却又蕴含着一个老银匠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普通物品作为核心道具,以郎木寺小镇为背景,围绕着一个老银匠嘉木措四处寻找继承人,却遭遇到一连串的欺骗、背叛甚至打击的故事,串起了老银匠的人生往事和他的银匠作坊的兴衰,以及藏地银匠行业的变化。小说中,从本地的藏族青年南木卡、道智到外地来的汉族小银匠来看,年轻人对传统手艺并不感兴趣,他们拜师学艺往往另有所图。屡遭挫败的老人只能一天天地在逼仄的小铺子里独自坚守着,面对着手艺濒临失传的前景,心中充满失望和怅惘。
创作《羊皮围裙》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困惑甚至伤感的过程,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藏区的作家,对于老银匠的遭遇和银匠行业的衰落感同身受,对那个传统手工业的时代充满留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现代工艺制造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手工作坊势必衰微,这似乎是一个大趋势。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在银器生产方式和制作技艺的新陈代谢上,而且更深层次地触及精神层面,涉及情感、伦理、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内在变化。《羊皮围裙》这篇小说表面上写的是新旧的工匠职业伦理与精神操守的冲突,进而带来的家庭婚姻伦理的畸变,实质上在这篇小说中我想表达的主要是:人心的变化。随着人心的变化,人性也被异化了。而让我感到难以处理的是:在藏地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与人物生存选择的必要性,对于种种新的现象,我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予以强烈地谴责。因为小银匠的选择似乎有某种新的合理性。我们该如何面对新的现实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我在这篇小说中重点关注的,但也是无力解决的。应该说,我的许多小说都贯穿着这一主题。
《缸里的羊皮》同样是一个与传统手工艺有关的故事,青年班玛次力凭着在监狱学到的制作翻毛皮鞋技艺,在家乡的牧场用缝纫机缝制皮袄,一度发财致富,但不安分的班玛次力不甘忍受皮革制作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梦想一夜暴富,走上冒险探宝之路,结果不仅钱财赔得一干二净,还毁了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这种变化,显然来自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外来的技术和金钱的诱惑使得宁静的村庄发生了波澜,生活在希望中伴随着失望,成功中伴随着危机。这篇小说里,我的关注点不再是传统手工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是随着现代技术的介入,人们原本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改变,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金手指》中,这种变化显示为外在的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草原上的牧民对这种复杂性的初次体验和感受。小说通过草原上老实本分的牧人拉加才让试图卖掉牛羊,凑足钱在县城开一家洗脚屋的梦想的破灭,折射出以“洗脚屋”为符号的县城生活的另一个灰色地带,反映出当代牧民对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怀疑和迷茫,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以及这种向往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夜如铅》也可以说是同类题材,只不过这篇小说的基调更为沉重一些,进城做生意的牧民桑吉不仅体验到了城市生活的复杂性,更是因为遭遇了商场中的诈骗而进一步体验到了人性之恶,它是像桑吉这样的牧民从稳定、单纯的草原生活环境进入城市生活要经历的“必修课”。
《铁匠的马》《谁厉害》《黑木耳》等小说中,我聚焦草原上农牧交汇地带的家庭故事,尤其是那些藏汉结合的家庭,如何从隔膜、冲突走向融合的故事。这些小说中,人物以半农半牧区为背景,因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生活矛盾与冲突,涉及到善恶、道义、情义、爱以及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样的冲突,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当下农牧区真实生活的反映。但我所着眼的是:有着不同身份及信仰的个体,是如何超越现实的物质困境、道德伦理困境、跨越情感障碍,而在生活、情感上完全融合到一起;如何在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中,使人性的真诚和温暖尽显光芒,从而彰显民族的珍贵的伦理传统和个体人性中那些深厚的民族美德基因。
无论银匠、铁匠,还是皮匠,这些手艺人实际上在农牧结合地的甘南已经很少了,然而我想写写他们。每一个小说都要有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要完成他的历程,要完全成熟,要站起来,同我交流、对话,甚至打架。我觉得自己是个万能的指挥者,可路到半途,他们就不大听我指挥了,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些人和事都不是偶然间遇到的,每个故事也不是陌生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在甘南大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来的真实表达,也是我对农牧区结合地的生存思考。我的作品中似乎没有好人,也似乎没有绝对的坏人,他们的好与坏都是随着事件的走向而变换着的,他们工作的细节我也是参与其中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或多或少代表了他们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地域的所作所为。
所谓逝者如斯,其实消失的并不是河流,河流浩浩荡荡,一如既往,不断消失的是住在河流边的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的文化与传统,失去的只是我们不断缩小了的眼光和奋斗的目标。因此,我努力在故事中补缺,在农牧区结合地的各色人物身上,以及各种事件中,还原出他们的劳动工具、生活方式,还有生存过程中所再现的苦难与温暖。更为重要的是,我还要在坚守中找到一个作家的尊严,让生存的艰难焕发出温暖,让沉重的生活焕发出温情。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