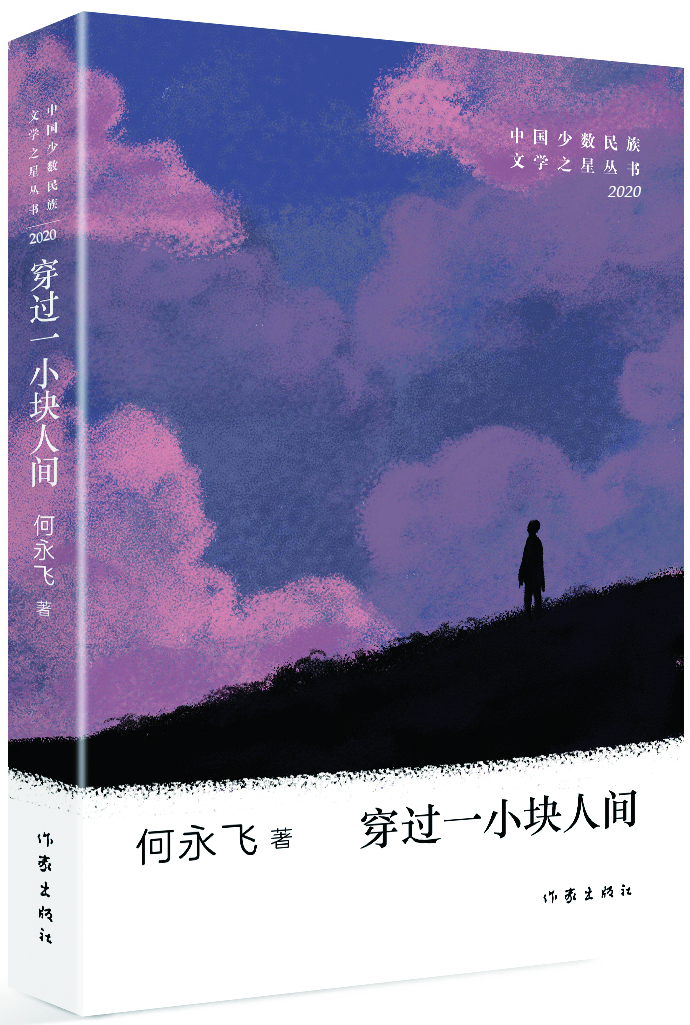
独坐水塘边,望天,风踏过脸颊,似乎有痕,暂避尘嚣,惬意滋生。云聚,又散,就像那匆忙的人群。草丛中觅食的鸟儿,警觉性极高,时不时地抬头,四周扭动,当看到我的眼睛,立即闪电般飞走,也许它是把我的眼睛误判成了枪口。
我有所思,又无所思。调整了一下坐姿,我把右手轻轻放在地上,手背突然如针刺一般地疼,查看原因,竟然是被一只蚂蚁咬了。自己跟它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不知为何要下狠嘴。灼痛,奇痒,红肿,还鼓起一个小包。蚂蚁并没有逃走,它似乎不怕我惩治,胆子真是大。若我想报复,蚂蚁瞬间就会成为肉泥,但我会为此感到羞愧,甚至耻辱。以自己之大,去欺负蚂蚁之小,是卑劣之举,表面上是赢了,其实是一败涂地。蚂蚁静观动态,见我不怒,也不言语,然后无趣地离开了。它没有任何歉意,但我依旧目送它。不好,蚂蚁落水了,在挣扎,它没有可抓的稻草。我毫不犹豫,跑过去施救。蚂蚁脱险,我心生欢喜,被它咬过的地方也不觉得疼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很差,恍恍惚惚,浑身无力,怀疑是得了什么重症。可去看医生,一切都很正常。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以经验判断,她认为我的魂儿走丢了,亟需去找魂。她在西北方向离家大约3公里的地方帮我找到了魂儿——一只蚂蚁,因为我曾在那里受到过惊吓。奇怪的是,母亲把找到的蚂蚁带回家后,我明显地感觉到精神开始日益好起来,最终恢复如初。更奇怪的是,母亲找到的蚂蚁跟我之前救起的那只蚂蚁长得很像,大小、颜色、眼神、动作等都差不多。如果真是同一只蚂蚁,那我救起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生命,而是自己的魂儿,何其幸运啊。
起初,我把写诗只是当作情感流泻的一种方式,内心积压的苦闷、伤感、愁绪、愤恨等需要排解出去,因为年轻的生命承受不了那么多,诗歌成为治疗自己暗疾的良药。那时我的很多作品不痛不痒,囿于小情小调,甚至还有应景之作。“小我”的写作格局,让我看不到出路和未来。重返茶马古道,西藏之行,似乎有一束亮光从顶门进入我的灵魂,让我看到了生命更加开阔的一面。从此,我把写诗当作自己修行的一种方式,不再顺从于小情绪,不再困于个人的狭小世界,以悲心观照万物众生,走向“大我”的写作格局。
失魂,已是时代普遍的症状。很多人的肉身奔跑得太快,灵魂被落在后面,距离隔得越来越远。最终灵魂丢了,还没发现,以致物质生活无比富足,而活得却不踏实,心神不宁,夜夜失眠,或常常从梦中惊醒。更有甚者,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还背叛或贱卖自己的灵魂。当然,也有可敬的守魂人。有一次,到偏远的一个古老村子采风,在触摸时光印痕和感受往事余温的同时,我用相机记录下所见的人和物。巷子深处走来一位背着箩筐的老人,箩筐里装满猪草,把她本来就有点弯的身子压得更弯。我举起相机,把镜头对准她,正要按下快门,这时她也发现了我,使劲向我摆手,不允许我拍照,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当地话。我有点纳闷,莫非拍照她要收费,现在很多旅游的地方,要拍照或合影,都需要付费,一切商业化,一切与钱挂钩。假如这位老人家也是这样,我真会有点失望。但还好不是,随行的本地朋友说,老人家不给拍照,是担心自己的灵魂被摄走。原来如此,我虽没有拍下想要的一幕,但老人家的身影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我们暂且不去评说“照相摄魂”的可信度,也不要拿“愚昧”这样冷冰冰的词去妄加评价和定论,老人家坚决守魂的态度和精神在当下显得弥足珍贵,是值得崇敬的。
作为写诗人,不能迷失本心。被誉为“灵魂的歌者”,对此,我欣然接受,不是说我有多崇高和伟大,也不是说我要给自己的诗歌写作贴上华丽的标签,而是我把它当作一种勉励,当作追求的一个方向。我想以诗找回自己和众人丢失的灵魂,以诗安放自己和众人漂浮的灵魂,以诗唤醒自己和众人沉睡的灵魂。也许会走得艰辛,也许会收效甚微,可我义无反顾,就算撞破头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也绝不后悔。
人神一体,我始终这样认为。不管是哪种宗教,我们信奉的主和神灵都来自人间,又回归人间,不然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在我出生和成长的滇西,被人们爱戴和敬重的神灵,都是生前有不凡经历和故事的人,他们就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肉身已化为泥土,而灵魂不灭,指引和照耀着后来者。我觉得,神有人性,而人也有神性。这点对我的诗歌写作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思绪时常会在人神之间穿梭,行善之人的面孔我想就是神的样子。或许是使命,或许是夙愿,在写人时我极力呈现其隐藏的神性,在写神时我又极力呈现其带有的人性。缺失谁,人间都是不完美的,也是充满危机的。
写诗,我有时会揭开这个世界的一些痛点,会把生命的残缺部分毫无保留地展现,会把人性的阴暗面翻出来,这不是说自己的心中充满怨恨,而是恰恰相反。正如贾平凹所言:“我经常讲,批判并不是要坠入黑暗,而是要引导光明。不是塑造一种仇恨,而往往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之所以爱这个世界,之所以爱一切生命,才含泪和忍痛这样做,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一切生命活得更加圆满和自在。
世间苦海,望不到边。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些苦看得见摸得着,有些苦却说不清道不明。无论社会如何发展,苦始终存在,物质能消除贫穷和饥寒之苦,但生死之苦,灾难、疾病、意外等之苦,还会伴随我们。都说苦难出诗人,但诗歌不是苦难的果实,否则就变成了苦生苦,苦上加苦,会让人活得更加绝望。写诗的人,心壁应该是柔软的,有悲悯情怀,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温度和亮光。
枪口生锈,戴着花环,飞走的鸟儿又回到了属于它的草丛中,觅食,欢跳。我起身,坦然回到尘嚣,不再刻意回避,头顶暗下去的天色在心间渐渐亮起。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