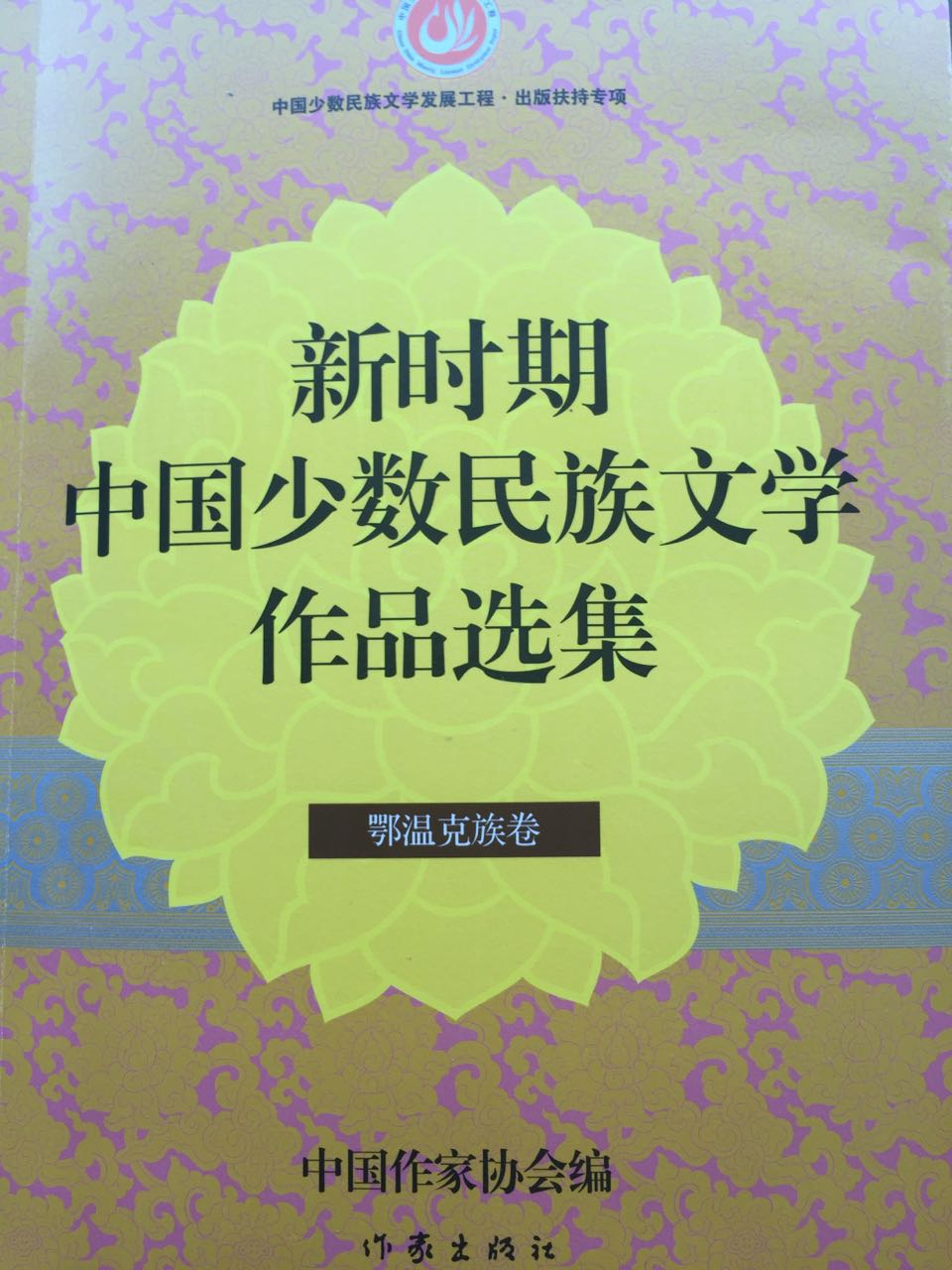
能够得到信任编选这本鄂温克当代文学作品选集并为之写序,对我来说是项殊荣,同时也显示了鄂温克作家的宽广胸襟——因为很多族别文学选集的参与者和评判者往往都是标准的“族内人”,而我这样的汉族学者只不过是个“外人”,似乎没有置喙的余地。鄂温克作家愿意倾听“他者”的声音,也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并不“躲进小楼成一统”,这可能是作为只有三万余人的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能够薪尽火传、赓续不绝的原因。
人数的多寡与文化的厚薄并无必然关系,正如经济的发达与否与道德修养的高低也没有因果链条,鄂温克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有着悠久口头传统的族群,一直没有书面文学,但是一旦开始了当代文学的历程,并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它的作家用汉语、蒙语迅速创造了一系列精彩的篇什,并且产生了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领军性人物乌热尔图。
我最初接触鄂温克文学就是从乌热尔图开始的,早先读《七叉犄角的公鹿》,在台北和北京的几次会议上也遇到过,偶尔交谈,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后来系统重读他的系列作品,才发现经过时间的淘洗,在1980年代纷纭变幻、杂花生树的文坛中勃然兴起又倏忽而衰的众多流派与作家中,乌热尔图反倒愈加凸显出鲜明的独特形象和文化意义。我曾经与几位做批评的朋友聊天说,当代文学在未来经过经典化后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中,必然有乌热尔图一席之地。
但鄂温克文学并不仅仅止于乌热尔图,乌云达赉、涂志勇、杜梅、安娜、涂克冬·庆胜、阿日坤、道日娜、贺兴格、哈赫尔、武波远、尼玛官布、杜金善、柳华、杜刚、杜国良、白淑琴、古新军、敖蓉、德纯燕、德柯丽、娜仁托雅等老中青几代人的写作已经逐渐形成了鄂温克当代文学的总体脉络。按人口比例算,这样的写作人数是惊人。当然他们中许多人的写作尚处于比较草率和粗简的阶段,如果从“纯文学”或者审美、技法等角度去看,可能不值一提;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文学”从来就不能简单地化简成审美、娱乐的消遣,它也是教育和认识的途径、自我表达和张扬精神的渠道,更是凝聚族群、振奋精神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小民族的日常状态,所关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达的欲望,情感诉求的倾向,内蕴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对这种传统的自豪与珍重。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只要不带着惯有的审美惰性和思想偏见,都能从哪怕最简陋的文字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灵魂,就好像从表面充满杂质的原石中发现珍贵的白玉。
2013年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到海拉尔的鄂温克自治旗的巴彦托海与辉河参加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民族”笔会,第一次亲密接触到鄂温克同胞们和他们生活的地方。我看到湛蓝的天空、广阔的草原、笔直的道路和安详的人们,也见到日益增多的能源企业来挖掘煤矿、采集石油留下的机器和斑驳的地表。一切都已经表明,鄂温克这一个地处中国边疆、早先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族群日益面临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现代性的变革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下山定居就开始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新媒体时代愈加激烈。很大程度上,鄂温克的传统因为被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的现代进程之中,而使自己成为一种被动废弃的传统。传统固然包含了生生不已、常变常新的一面,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却不得不在时势大于人的环境中各自面对这种命运,承受着变迁所带来的阵痛。
因而,从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时期”以来,鄂温克文学第一波浪潮直到当下,现代性中的内在冲突与裂变就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以两种形式被表述出来:在历时层面是传统与现代、代际之间的矛盾;在横向层面是族内共同体与外来者、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扞格。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刚健中蕴含深沉广阔的思索。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现代性的失落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鄂温克写作主题,只不过它更增添了一种挽歌式的怀旧色彩和忧郁笔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势进入,造成了执拗性的退守形态,使得越来越多的鄂温克新作家投入到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强调之中,因为差异性才是应对全球通约性的资本和基点。但这无疑使得写作主题狭窄化和单一化了,文化寻根和认同的强势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压抑,让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主题被掩盖。因为虽然是个边缘、边远、边境的少数民族,鄂温克始终都不是自外于主体、主流、主导性的文化与话语之外的,它的命运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忧伤与欢欣、哀愁与希冀、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从1980年代涂志勇的小说《彩虹在远方》中可以读到类似“改革小说”式的困惑、挣扎、探索、创新的勇气与担当的精神,那是一种带有理性反思色彩的大写的主体在沉思自己及自己命运的命运。他的《最后的猎人》与杜拉尔·梅的《那尼汗的后裔》等则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一种新型的认同感开始展开,开始从本民族的渊深的传统里发掘资源,与乌热尔图中后期开始的非虚构写作转型齐头并进。这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既是“鄂温克文学”,也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回响的是时代的跫音。在庆胜的自然主义色彩浓郁的故事白描中,在德纯燕“离散”式的写作题材中,也可以感受到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与心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鄂温克文学体现出来的宽厚博大、顽强坚韧、反求诸己、淳朴刚健精神,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讲述了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国故事”。这是鄂温克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鄂温克文学也有它的独特性的一面,即它们总是会带有天然亲近性的本族群文化书写,包括景物、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俗、信仰、禁忌等。这些描写不仅绘声绘色地提供了让人如深入其境的代入感,也是对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播,对他人起到了认知和教育的功能。这是特有的、无法替代的新鲜特质,比如森林的场景和意象、猎人出猎的方法和过程、宗教活动中的萨满跳神……都增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组成和多样元素。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学书写中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与情感信息,比如安娜《绿野深处的眷恋》就涉及到1960年代初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蒙古同胞收养三千多名上海、常州、苏州、无锡的孤儿的背景。在鄂温克牧民家中长大的上海孤儿铁木尔姑娘面临着类似于张贤亮的《灵与肉》中许灵均式的选择,这虽然是大时代的小插曲,却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还是不知道呢?还有《静谧的原野》中汉族知青李玉与鄂温克牧人桑登老爹、小妹妹塔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不正是中国各民族在交流互动中和谐共处的生动写照吗?但是多年以来,这些历史,以我有限的观察,似乎只在内蒙古导演的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与电影《额吉》中有所体现,对于这样有着特殊意义的题材,他们是遗忘了,上海的作家、艺术家好像集体失语了。
文人的势利和世故,确实是我们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普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不遗余力的进行扶持,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文化惯习和“文明等级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野蛮”、“没文化”,而是在既定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批评者缺少知识储备和同情性的关怀,而少数民族题材也往往缺乏商业性的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广泛的关注,所以它们难以赢得主流批评者、研究者的梳理与阐发,也很难作为一种国家性的文学知识进入到主流文学体系之中。然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足以自豪的文化经典,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大史诗(当然,我不怀疑很可能有许多作家、批评家压根连这些都不知道),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著名和新锐作家,比如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阿拉提·阿斯木、叶尔克西、夏曼·蓝波安、瓦利斯·诺干、巴代、光盘、金仁顺、田耳、马金莲、了一容等。正是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反映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的现场。在缺名少利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中,一般只有少数专门研究者去注意他们,并且还是集中在那些名家身上,鄂温克作家中被研究者注意和了解的更是屈指可数。所以,这本选集兼顾了许多并没有“名气”的作者,以及以蒙文写作的、几乎很少被汉语读者看到的作品,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自1980年代以来,鄂温克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这同时也是呈现完整的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举措。
这里面的作品当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从文学史料的角度来说,我们尽量求全面,而不是以某种单一的审美标准做取舍。尽管如此,限于篇幅,还是必然要遗漏一些作品,它们散见于等各种文学报刊,也可以见诸苏伦高娃编的《鄂温克族文学作品选》。如同前面所说,在回首往事、瞻望历史和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鄂温克文学能涌现出更多发挥想象、着眼未来、主动将自己个体及族群文化遗产融入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思考的作品。毕竟,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主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关注本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在继承中有扬弃和超越,像那些文学先辈们一样志存高远,在一己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中把握时代脉搏,脚踏草原大地,瞻望前行之路,毕竟每个人都命运相连,那些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各民族同胞其实都在经历相似的命运。这本集子留下四十多年来鄂温克文学的行进足迹,作为将来新作品出现的基础立此存照。
在此,感谢岱钦先生为鄂温克族作品翻译成汉文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把鄂温克民族独具的生产、生活、习俗方式呈献给读者。感谢鄂温克自治旗文联苏伦高娃主席及其同事们的大力协助和细腻工作,他们的努力不仅在于为本民族留下一份文学遗产,也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事业提供一份见证。
刘大先
2014年11月15日于北京八大处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