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视野整理研究《格萨尔》史诗——访藏族学者降边嘉措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4-07-04 作者:黄尚恩

降边嘉措 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1950年参加解放军,经历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1956年到北京民族出版社,从事藏文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直到1980年。1980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并被录取,后来主要从事《格萨尔》史诗研究和翻译工作。曾出版《〈格萨尔〉初探》《〈格萨尔〉的历史命运》《〈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等学术专著。主编有《格萨尔》藏文精选本(40卷、51册)、《〈格萨尔〉大辞典》等。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分别获得第一届、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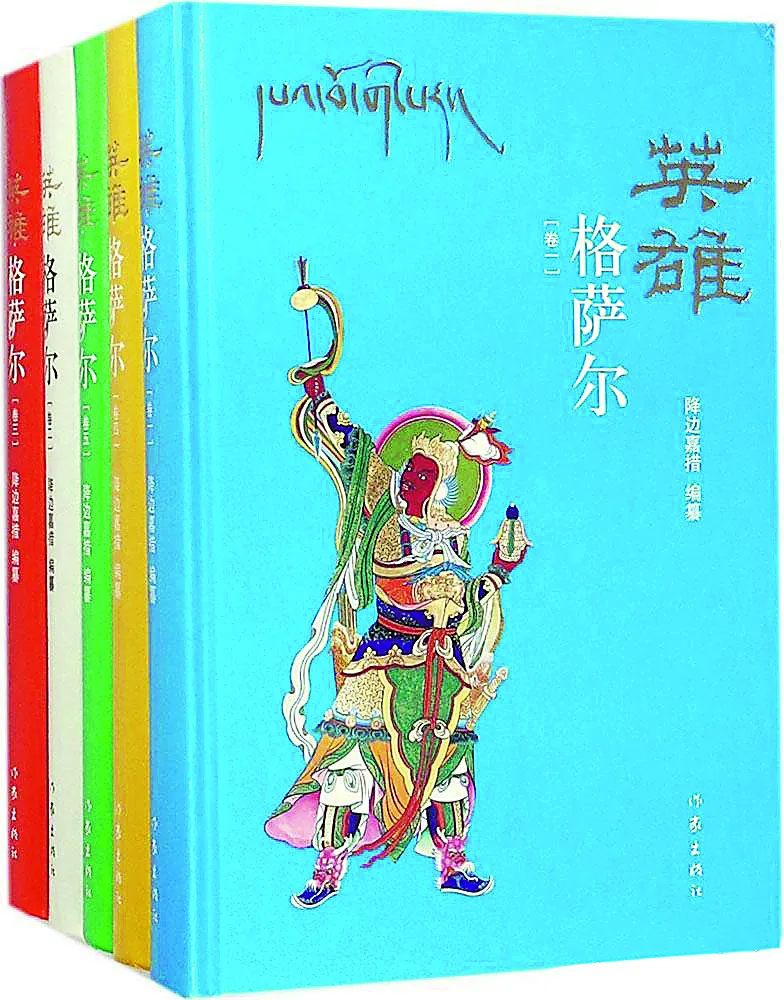
《英雄格萨尔》(全5卷),降边嘉措编纂,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
从翻译工作转向《格萨尔》史诗研究
记 者:降边嘉措老师好,您的身份非常多元,包括翻译家、学者、作家等。您起初主要是做翻译工作的,参与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和《红旗》杂志等文献的藏文翻译工作,并在一系列重要场合中担任翻译。您的翻译能力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降边嘉措:我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既教藏语也教汉语。而且我们老家位于金沙江边,位置比较特殊,当时有很多来往的商人,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比较显著。因此,我们那里的很多人藏语汉语都会说。1950年,我12岁,小学毕业,因为没钱去离家比较远的地方读中学,所以就随哥哥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我们老家说的藏语属于康巴方言,虽然平时也经常从来往客人中听到拉萨话,但它毕竟属于卫藏方言,与康巴方言还是存在很多差异。因此,我们到了拉萨以后,为了工作之便,部队领导要求大家学习拉萨话,特别是书面文字。就这样,我就在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学习藏文。完成学业之后,我开始当翻译。1954年,又被选派到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学习。毕业后,就到北京专心做翻译工作。在民族出版社工作的20多年里,参与翻译了一系列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央重要文件。可以说,我的翻译能力,主要通过“学中用、用中学”锻炼起来的。
记 者:1980年,你从民族出版社调到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和原因,让您决定从一个翻译家转变为一个研究者?您此前的履历与《格萨尔》史诗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为何会专门选择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降边嘉措:当时,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刚成立不久,并在全国招考,我考了第一名。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心求变。我在北京从事了24年的翻译工作,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做出一些改变。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后来,除了工作上的翻译任务以外,也翻译一些诸如《格萨尔》故事、《萨迦格言》《水树格言》以及人物传记等,也喜欢看汉文典籍,觉得应该适合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到民文所报到没多久,所领导贾芝先生就把我叫过去,交代工作任务。他说:“所里之前还没有一个藏族的,你是第一个。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格萨尔》研究。这是你接下来要做的重点工作。”我之前没有专门研究过《格萨尔》,但从小就和它有接触。在藏族地区,《格萨尔》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所以,过去藏族有一句谚语,“岭仲(《格萨尔》)是人人口中的事”。当时有很多信徒和说唱艺人,他们要去拉萨、冈仁波齐朝拜,往往路过我们老家,晚上就聚在一起说唱。我们就在旁边听着,对史诗中的很多内容都有印象。
我的翻译经历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在24年的时间里,我认真学习和翻译马列著作,并通过翻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我提出,应自觉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事《格萨尔》研究,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研究的科学体系。
《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记 者:您从1980年代起,就参与《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2013年,《格萨尔》藏文精选本(40卷)的集中推出,是《格萨尔》史诗整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标志。我们知道,《格萨尔》篇幅特别长,各个说唱本的差异也很大。当初项目组如何确定精选本的篇幅?如何处理不同说唱本之间的异文?
降边嘉措:从1983年至2013年,《格萨尔》藏文精选本的编纂工作历经30年。这套精选本共40卷、51册,近60万诗行(假若翻译成汉文,约为2000万字)。确定选本的篇幅为40卷,主要依据有二:第一,除去各种“异文本”和“变体”,《格萨尔》的分部本大约有120多卷,从中精选三分之一,是40卷。第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不丹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了30卷的《格萨尔》汇编本。我们国家是《格萨尔》的故乡,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总应该比不丹做得更好一些,内容更丰富一些。
无论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木刻本,还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同一部故事又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因而产生不同的本子,我们将它称之为“异文本”或“变体”。“异文本”,少则一两种,多则有好几种,甚至有的内容出现了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如《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霍岭大战》等部分,在整部《格萨尔》里是比较受欢迎、流传最广的,因此,演唱的艺人也很多,西藏的扎巴、桑珠、玉梅、曲扎,青海的才让旺堆、昂仁、古如坚赞、达瓦扎巴等说唱艺人都经常演唱这几部。在主要内容、主要人物、基本情节相同的前提下,又有演唱者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演唱风格。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以当代杰出的民间艺人扎巴和桑珠两位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以保证整部精选本思想内容的完整性、演唱风格的统一性和语言艺术的和谐性。同时,也参考了才让旺堆、玉梅、昂仁、古如坚赞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和长处。
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协调、拼合。比如说,这个故事,可能A版本讲得更好;但到了下一个故事,又变成B版本更好了。这就需要将唱得较好的段落进行“剪裁”和拼接。而且,有时候所依据的底本,故事有残缺,也需要结合别的说唱本来补全,让故事的逻辑更加顺畅。因此,这个工作难度就很大。一方面,需要邀请西藏、青海等地的大量人才来参与,需要做好各种沟通协调工作。另一方面,有些人说风凉话,“你进行大量的拼贴、加工,你这就是作家文学,不是民间文学了”。但最终,我们顶住了压力,坚持下来了,完成了这一卷帙浩繁的工程。
记 者:从1986年的《〈格萨尔〉初探》到1994年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再到1999年的《〈格萨尔〉论》等,您推出多部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专著。您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也于2017年出版。您是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研究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在您看来,国内的《格萨尔》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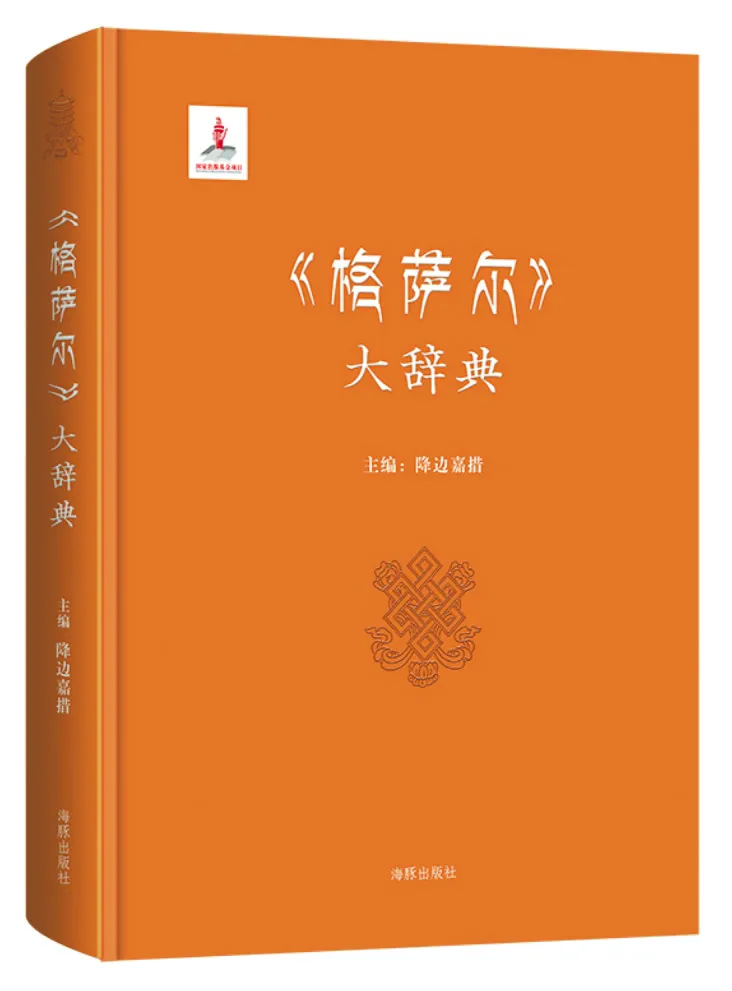
《〈格萨尔〉大辞典》,降边嘉措主编,海豚出版社,2017年3月
降边嘉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格萨尔》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彻底改变了我国《格萨尔》和史诗研究的落后局面。《格萨尔》研究成为我国藏学研究领域和民族、民间文学领域极为活跃的一个学科,而且这个学科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为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正如一句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将要做的事,比已经做过的事要多得多。”一是要继续做好扎巴、桑珠、玉梅、才让旺堆等艺人说唱本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二是做好《格萨尔》的汉文翻译出版工作,真正推动《格萨尔》的传播和研究。三是进一步加强相关人才培养,使《格萨尔》事业后继有人。
说唱艺人是史诗最忠诚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
记 者:说唱艺人是《格萨尔》史诗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因素。很多媒体在报道说唱艺人时,往往说他们经历了一场梦,大病一场,然后就突然顿悟,拥有说唱史诗的能力。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降边嘉措:《格萨尔》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许许多多民间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的。他们行走在高原山川河谷,高歌吟唱。一代代说唱艺人,将故事传颂千年,远播万里。他们是史诗最忠诚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民诗人。说唱艺人的记忆之谜,是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这些诗句是怎么出现在艺人脑海里的?不同类型的说唱艺人,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类叫“托梦艺人”。这类艺人大多数说自己在少年或青年时代做过一两次神奇的梦。做梦以后,一般都要大病一场。病愈之后,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讲《格萨尔》故事。从此,他就与《格萨尔》史诗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类叫“顿悟艺人”,他们是“忽然醒悟”,因此,他们的记忆、他们所讲的故事,就有短暂性和易逝性。这类艺人不像“托梦艺人”能讲很多部,能长期讲下去,而是一般只能讲几部,有的只会讲一、二部,而且只讲很短一段时间。有的艺人在一个时期里讲得很精彩,在另一个时期又讲不出来,像换了一个人。第三类叫“闻知艺人”,他是听别人说唱之后学会的。这类艺人一般只会讲一两部,或某些片断。对于“闻知艺人”,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对于“托梦艺人”和“顿悟艺人”,我们容易把他们过度神秘化。特别是一些媒体人,没有认真采访,加上语言也不大通,就胡写一通。实际上,“托梦艺人”和“顿悟艺人”的出现,也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这里“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等。概言之,也就是艺人和史诗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当然,这其中还存在着基因遗传和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托梦艺人”还是“顿悟艺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梦”或其他某种机缘的触发下,把过去关于史诗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积累展现出来。我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这些史诗来源于人民的创造实践,而这些说唱艺人是“史诗环境”所锻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
记 者:有学者根据“口头程式理论”提出,说唱艺人之所以能够讲述那么长篇幅的史诗故事,是因为史诗中有很多模式化的叙事结构,而且艺人在讲述过程中可以使用套语。您认为,“口头程式理论”能够有效解释说唱艺人的强大记忆力之谜吗?
降边嘉措:作为说唱艺术的史诗,不同于作家的创作,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形成一定的程式,这的确是艺人们容易掌握和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整个《格萨尔》里,除去《天界篇》《英雄诞生》《地狱之部》等少数几部外,一般都是一个分部本讲一个战争故事。一个战争故事基本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缘起,讲战争的起因;二是战事迭起,这是故事的主体;三是结束,且结局总是格萨尔胜利、妖魔失败。这构成了三段式的故事结构。战争的参加者往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界,包括天神降预言,在暗中保护助战,乃至派战神直接参战;二是人界,包括以格萨尔为首的岭国将士和敌国将士;三是龙界,包括龙王,以及鲁、念、赞等龙神、地方神和土地神。
至于史诗的每一个中心唱段,也往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开头的赞辞、自我介绍;二是中间的核心情节;三是结尾的祈祷词。还可以举出若干例子,说明很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只要抓住这几个方面,就抓住了重点,抓住了故事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就可以讲下去。即使忘了若干段落或词句,也无关紧要,不至于接续不上。而且在类似的地方,可以使用很多的套语。这种记忆方式,大概是史诗艺人们的共同特点。
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有了程式,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去讲史诗。说唱艺人能记住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名、地名、武器名,将这些框架填实,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拥有强大的记忆力。说唱艺人们生活在史诗诞生的文化环境中,自然会受到熏陶和启示,锻炼自己的记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常常云游四方,走遍万里高原的山山水水,雄伟壮丽的大自然陶冶着他们的情操、净化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同大自然融为一体,胸襟开阔,思想专一,摒弃杂念,因而能够强记博识。
在“传说”与“传记”、“真实”与“虚构”间寻找平衡
记 者:四川正组织作家、学者撰写历史名人丛书。“格萨尔王”被列为其中的一个人物。您在参与书写“格萨尔王”故事和传记的过程中,有什么样新的感悟?
降边嘉措:这套丛书的格局是为“一个名人”写“两本书”,一本是偏故事性的,另一本是偏传记性的。故事性的书,相对好办。我之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英雄格萨尔》,基本上把格萨尔一生的重要事迹都进行了梳理,不仅讲了格萨尔从诞生到逝世,即从天界到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天界的全部过程,还讲了英雄诞生之前和逝世之后的故事。有了这样的基础,这次再写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书,就相对轻松一些。但是,格萨尔王的传记就比较难推进。因为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传说色彩很浓的人物,你很难找到确切的史料来进行传记的书写。唯一可以依据的是,传说都会经历“本地化”的过程,在当地拥有对应的“传说核”。在藏族地区,就有很多与格萨尔有关的风俗、遗迹。比如,在我老家那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石头,上面有个脚印,据说是格萨尔王的脚印,传说格萨尔王把一只脚放在石头上面向远处投掷石头。那么,我写格萨尔王的传记,只能去寻找格萨尔王传说“本地化”过程中所留下的点滴依据。这是“传说”与“传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有趣博弈,也算是比较深刻的写作经历。
记 者:作为作家,您之前创作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报告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二次长征》等,都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这些创作都和您个人的参军、进藏经历,以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这背后体现了您什么样的创作观念?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降边嘉措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
降边嘉措:我的写作与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从少年时代起参加人民解放军,走上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艰难而悲壮的征途,是这个巨大而深刻历史变革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人。长篇小说《格桑梅朵》里面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在回忆录《感谢生活》里,我曾介绍了这些原型与《格桑梅朵》中一些人物的关联。《格桑梅朵》从开始写作到最后顺利出版,经历了20年的时间,是一部对我自己来说不得不写的作品。我要把它献给那段特殊的岁月、那群特殊的人。此外,我也写了很多报告文学、传记作品,这是因为我认识了很多的人,熟悉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有直接的交往。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下了功夫。我要写的是大历史,而不是小故事。因此,我尽量做到把人物放在历史长链条和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今后,我还要继续写一些传记作品,因为还有很多的人还没写,还有很多的史料还未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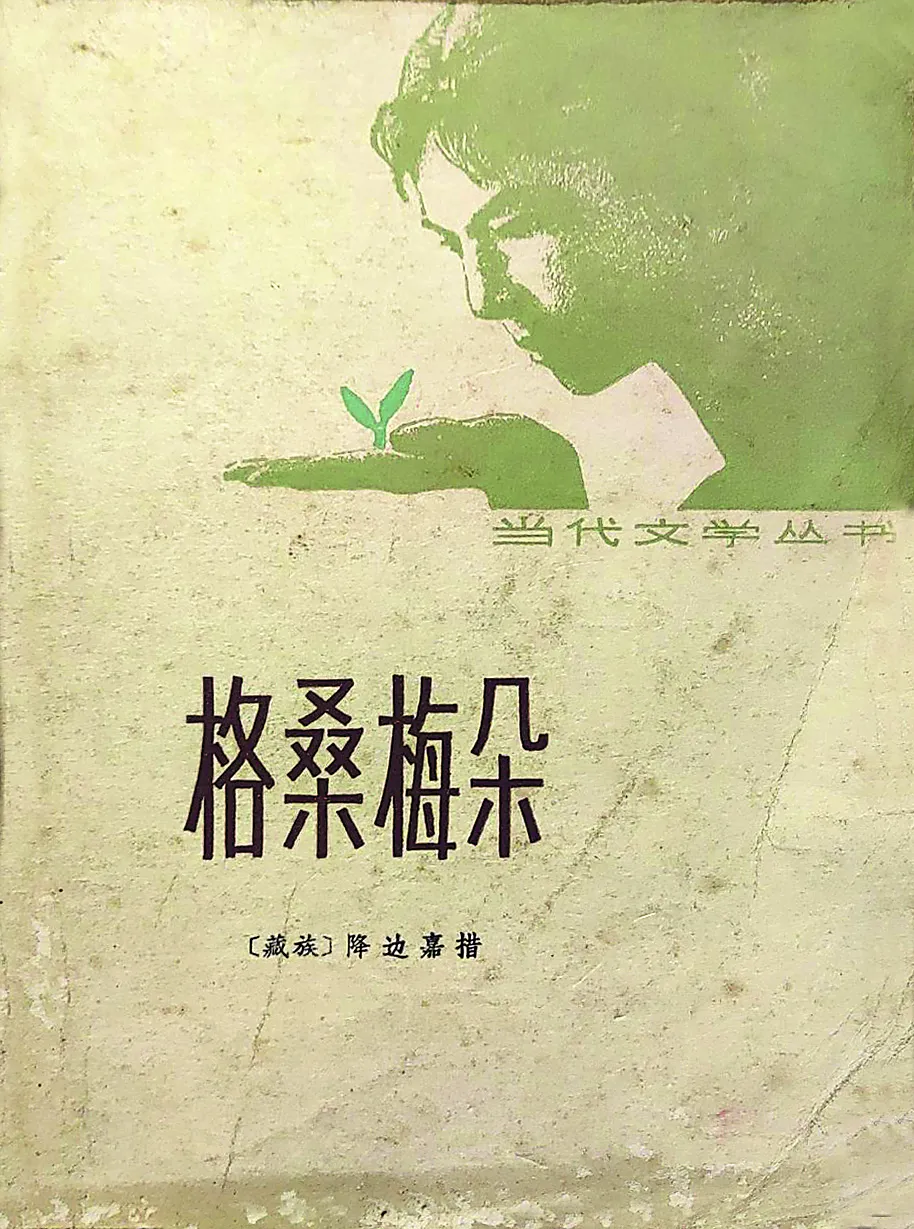
《格桑梅朵》,降边嘉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
文章来源:《文艺报》2024年7月3日5版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


